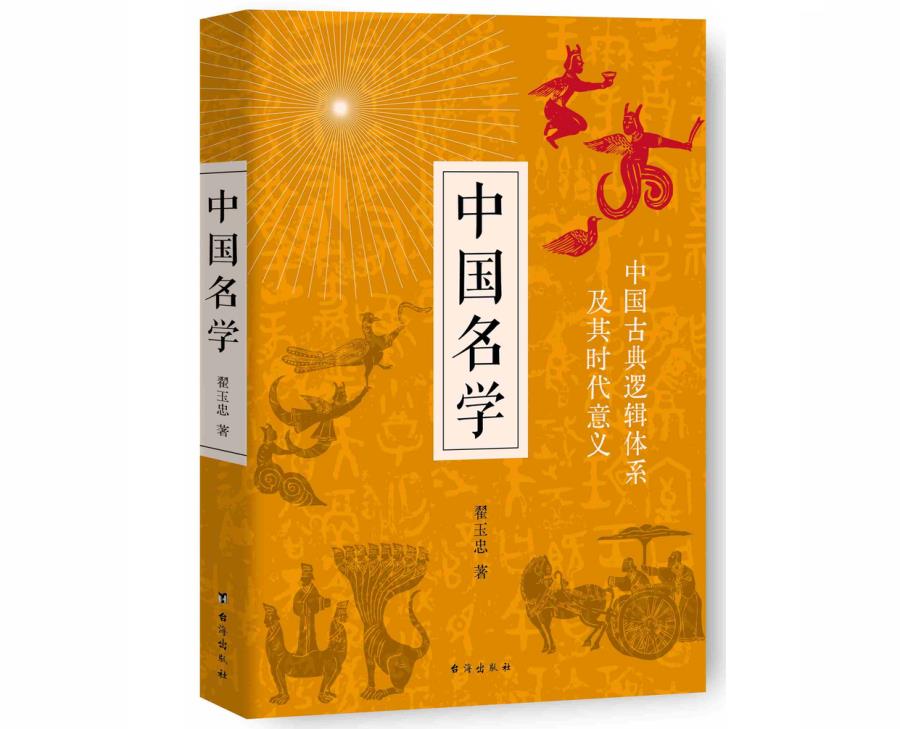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并入我们的版图呢?我们掌控更多土地的最好方式就是:借助于宗教手段,然后派出军队。”17世纪初,葡萄牙国王谈到东方国家日本时作如是说。【1】 这段话透露了过去500年西方殖民主义的本质特征:一手捧托着《圣经》,一手挥舞着刀剑;以文化殖民开路,达到征服人心、掠夺资源的终极目标。19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知识体系逐步取代的《圣经》,成为西方“教化全球”,文化殖民的主力军。 直到21世纪的今天,西方学术仍垄断着中国大学的讲堂,甚至中国古典学术本身也被西方学术格式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多年来,我们以孔子所传四科之学为基础,全面整理、复兴中国文化体系的源动力。 回想2001年2月,笔者辞去稳定的工作,离开家乡来北京寻找宇宙人生大道,迄今已经23年。这23年是一次备尝艰辛而激动人心的学术远征! 我和同道者们翻越了三座大山,最后抵达了2500年前轴心时代中华原文明的高峰,看到了中华文化智慧、安乐、德行三位一体,内养外用不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普世大道,并以“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的形式,奉献全世界! 翻越近代西学、宋明理学、两汉经学的大山太难了,我们披荆斩棘,历尽磨难,遍体鳞伤地走了过来。中途看到太多学者游魂般生活在西学、理学、经学的阴冷森林里,一生都不能出来。 第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近代西方学术,具体地说是大学中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学术。我们从孩童时代入学到大学毕业,乃至读博士成博导,必须深入这座大山。近代学术形成于西方殖民主义时代,面对中国这类非西方世界,西方人的主导思想是“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结果学人只会讲述西学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讲清楚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更不能说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 比如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无论是“中国”还是“人”,受过现代教育的国人都是从西方意义上理解的。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人则理解为宇宙中渺小的灵长类动物,信仰了基督教的,还会说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传统上我们将“中国”理解为以普世文化(人伦礼义)为标准的天下,“人”则理解为与天地并列、参与天地运化的最高存在。而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已经被“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的西学逻辑屏蔽。我们讲的“中国人”之名,实际是在说西方的“Chinese”之实。 从民主观念到人性善恶,我们的全部意义世界都是西方的,对应的则是西方文字——这就是中国话语权旁落、软实力疲弱的根本原因,用西方的“名”,解释迥异的中国之“实”,名实怎能不混乱! 早在196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就建议,不要用希腊拉丁词根来描述中国,而最好使用“中国形式”。包括中国学界在内,似乎没有一个人回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 我也不喜欢把“自治的”一词应用于(中国)乡村社区,因为我认为它只是在非常确定的界限内才符合实际。事实上我们急需发展一些全新的专业名词。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社会状况是鲜为西方人所知的,而在创造这些新的专业词汇时,我建议最好使用中国形式,不要继续坚持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根来描述非常不同的社会。【2】 李约瑟博士不会想到,以西方概念解析中国现实,竟会在中国成为基本学术范式。尽管早在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警告国人,用西方学术(“洋货”)整理中国故有思想,在各个学科中都会产生名实不副的现象,结果只会是“画我不是我”,遮蔽中国文化本身。他说: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3】 我们必须回归中国的意义世界,以及基于此意义之上的话语体系。否则,学人一生困在西方学术的庐山之中,永远不会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今日中国学界之蒙昧,可以套用唐代高僧黄檗希运禅师的一句话:“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中国学者“终日言说,未曾吐一句中国话!” 我们是如何翻越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这座大山的?关键是坚持“中体中用,中西互济”这条学术路线不动摇,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内在的逻辑性和统一性全盘托出,彻底打碎了西方人眼中中国只有思想碎片,没有系统学术理论的判断。 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学术体系,且整体上更为完备。因为诸子百家相辅相成,相须为用,内圣智慧和外在事功合一,而西方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则长期处于巨大张力之中——西方学不术则断分化、细化,呈碎片化趋势。 第二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宋明理学。2000年前佛教进入中国沿两条路线演进:一是佛教自身的中国化。二是中国文化的佛教化,后者催生了宋明理学。 表面上宋明理学激烈反对佛教,本质上它是佛教化的儒学,用佛教的个人启示取代了中国内外兼修,积善成德的生活方式。难怪清代大儒颜元批评朱熹:“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4】 宋明理学如何将中国文化佛教化的呢?首先是学习佛教判教将诸子百家异端化,结果包括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王经世之术”【5】百家之学,从理论到实践层面被丢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学独尊”,理学家成为道统化身!然后通过“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方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中国文化佛教化——其桥梁是中国化的禅宗。 从二程和朱熹开始,理学家就特别看重《大学》《中庸》,认为二者是圣人口耳相传的大法,初学者掌握真理的门径。朱熹《大学章句》认为,只有《大学》告诉学人修行的次第:“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正是在修行次第上,宋明理学家颠倒了本末。大学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成了本,“止于至善”成了末。因为按照禅宗理论,认得妄心,识得本心是基础。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过:“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6】 所以朱熹也在中国文化中“制造”出妄心和本心,即人欲和明德,有时也称人心或道心。《大学章句》解释“明德”时,彻底背离了“明明德(行)于天下”的《大学》本义,将平天下的实际事功转化为个人修养,“明德”成为本心,“本体之明”。文中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对于《中庸》,朱熹背离古人“心是谓中”的观念,将“中”解释为行为上的不偏不倚,混淆了内外。 “中庸”的意思如黄老之“心术”,讲用心之道,心之用。《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中庸章句》题解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进一步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简直是时空穿越的小说,因为子思死时,孟子尚未出生! 过去十几年来,我和同道合作,写了大量文章,欲正本末、明内外,将宋明理学“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错误修正过来。 今天学人一言中国文化就是理学化、佛学化的儒学。不仅普通百姓不能区分理学、儒学、孔学、经学的关系,一般学者也不能区分——这是宋明理学家、明末耶稣会士、清末民初中国学者、1949年后港台新儒家和改革开放后大陆新儒家用以突出中国性、否定中国文化普世性的共同“制造”。【7】 这种用以指称中国文化的“儒学”在学理上排斥诸子,排斥外在事功,是宋以后国运衰弱的思想根源,这不是小问题,是关系国运的大问题——这座大山跨不过去,会有亡国的危险! 第三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两汉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件事如汉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一样,影响长达2000年之久。贬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国家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性格,塑造着国家政治、个人伦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民国初年。蒙文通先生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论经学遗稿三篇》说: 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8】 汉武帝的文化政策是成功的,亦有沉重代价。一是“表彰六经”,经学成为利禄之途后,经学迅速僵化、繁琐化和玄学化。两汉儒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儒学不断方士化的过程,董仲舒已将阴阳五行同灾异感应联系起来,到东汉,谶纬之学大兴,搞得经学乌烟瘴气。经学成为仕进之途后,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地盘,经学家株守家法、师法,包括西汉末年反对古文经学,都是为这个目的。东汉王充不禁感叹:“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指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笔者注),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即根荄,犹言根本——笔者注)。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9】二是“罢黜百家”导致经学与子学的有机联系断裂。西汉东平思王刘宇(?—前21年)上书朝廷,请求诸子百家图书。大将军王凤对皇帝说“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10】反对将这类书给东平思王,可见时人已将经学与子学对立起来。 经学失去子学之流,必成为一潭死水,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比如儒者多言禅让制,而不知禅让制本质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后来发展为秦汉发达的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因为那是法家的主张,所以儒家要反对。如果我们不从社会功勋制角度理解禅让制,那么禅让制只能作为神话存在,更别谈用它解释21世纪中国选举制度了! 可以说,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埋下了经学僵化,后来成为僵尸的祸根! 当代学人所做的,就是用西方专科学术埋葬这具“僵尸”。名曰“整理国故”,结果今人已经连经学的面目都不识了。因为“经学僵尸”已成尸块。经学就是经学,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选举制度与中国人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密不可分,哪能将经学进一步肢解为哲学、史学、文字学之类。蒙文通先生大声呼吁: 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11】 我们不能追随五花八门的“新儒家”,罢黜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独尊理学或儒术,要“会通经子,表彰六经”,回归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大经大法——那是中华魂,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本!亡经学就是亡文化、亡天下! 还我文化山河,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必须翻越阻碍中国文化返本开新、守正出新的三座大山! 过去20年来,我们过五关斩六将,降魔捉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才胜利登上了轴心时代中华原生文明的峰巅——以“孔门四科”为纲领的中华文化! 这次我们重新整理中国文化与周代面临社会大失序(礼崩乐坏)的孔子不同。首先,孔子是以西周王官学诗、书、礼、乐“四术”为核心整理中华文化的,我们则以“孔门四科”为核心。 但孔子并不以“孔门四科”教学生,它还是以西周王官学传统的“四术”为主要教学内容。《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礼记·王制》说:“乐正(大司乐,相当于古代大学校长——笔者注)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正是从诗、书、礼、乐中,孔子培养出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这四类特长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之为“异能之士”),后来演化为诸子百家。所以我们按“孔门四科”整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中国文化,才能做到“纲举目张”! 其次,孔子有明确的理想标杆,他说:“周监(通“鉴”,借鉴——笔者注)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周朝集夏、商两代之大成,所以孔子尊周礼。孔子上下求索,周游列国,力图恢复周朝那样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礼义王道),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他极伟大之处。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东方,要在不失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开放地学习西方,择善而从,所以关键是“明东西”。融入世界,世界才会认可中国文化内在的普世性——光返本而不能开新,如同闭门造车! 也因此,孔子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整理方针。但我们不同,面对西方系统化专科学术,我们必须“既述又作”。比如经学,在民智大开的时代,必须牢牢抓住经学作为“先王经世之迹”【13】本具的大众性、实用性、世界性特征,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重新阐释。经学如同今天的政府公文,怎会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经学是小众的无用之学?它面对的是大众和天下,必有其实用价值。经学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将之作为榜样、模板,解释过去指导未来——经学是中国文化的DNA,中国历史和现实不过是经学的复制和表达。我们忽视甚至否定经学,实际上剪断了联结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脐带!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位列“孔门四科”言语科的名学是人为一切知识和社会活动的基础——历史上儒家也被称为名教,以名为教;法家也被称为名法之学,形名法术之学,足见名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地位。 名学是文化复兴的起点,文化自信的基石,文化安全的长城。何以这样说? 因为没有名学,我们就无法摆脱以西式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学术,以西方之名释中国之实,结果只能使中国历史和现实成为西学研究的对象,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沦为西学的附庸。何以谈文化复兴! 因为没有名学,我们就解释不清楚以名位为基础的教化,中华名教(伦理道德)的起源。也解释不清中国古典政治体系刑名法术之学。结果中国的社会观念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倒影或阴影。何以谈文化自信! 因为没有名学,我们就不能清除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众多恶毒不实之名(鄙名和伪名,详见本书“名学十三篇”),没有了思想观念的“海关”“防火墙”,何以谈文化安全! 本书是两千年来对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的第一次系统整理。今天名学主要保存在墨家和名家中,我们打破古人以书分类的诸子界线,将二科中相关内容合而为一,由此找到了名学的推理形式——名学成了可以活学活用的知识工具! 201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相关研究成果《正名:中国人的逻辑》第一版,十年过去了,《正名:中国人的逻辑》早已绝版,网上甚至炒到了三五百元一本。 因此,我们发心再版该书,欲让更多人学习名学,运用名学。有了名学这个逻辑工具,中国在精神上才能真正崛起,中国文化才能贡献于世界。 本着为大众做学术的人生信条,笔者对《正名:中国人的逻辑》第一版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学术性很强,且带有资料性质的“《形名杂篇》译释”“《墨经》名辩精要”两大部分,增加了“正名顺言篇”。 “《形名杂篇》译释”是对伍非百先生《中国古名家言》“形名杂篇”部分的阐释。《中国古名家言》是近代名学研究巨著,修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再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墨经》名辩精要”是在谭戒甫先生《墨经分类译注》的基础上,对《墨经》中名学部分的辑录。《墨经分类译注》由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新增的“正名顺言篇”,除了第一版附录中的四篇文章,还收录了过去十年来笔者研究名学、应用名学的一些文章,目的是让读者看到名学的现实意义所在。 这一调整,使本书更具有可读性和实用性。 最后,感谢上海的李网兴先生为本书顺利出版提供的支持,以及太多友人的鼓励和帮助! 德不孤,必有邻。我们的使命漫长而艰辛,但没人能阻止内圣外王一贯的普世大道升起在21世纪东方地平线上! 在世俗性全球化大转型的时代,这一古老而崭新的文明范式必将照耀全世界! (《中国名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纪录片:《日本神秘帝国的回忆》(Japan Memoirs of a Secret Empire)第二集,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411272J?p=2&vd_source=7bd3312d933504035c126a92754b83a4,访问日期:2024年3月7日。 【2】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徐汝庄译,载《自然杂志》1990年12期。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4】颜元:《朱子语类评》。 【5】《史微·卷一·百家》。 【6】《坛经·行由品第一》。 【7】参阅詹启华(Lionel M. Jensen):《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8】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9】《论衡·正说篇》。 【10】《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11】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2】《论语·八佾篇》。 【13】《史微·卷一·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