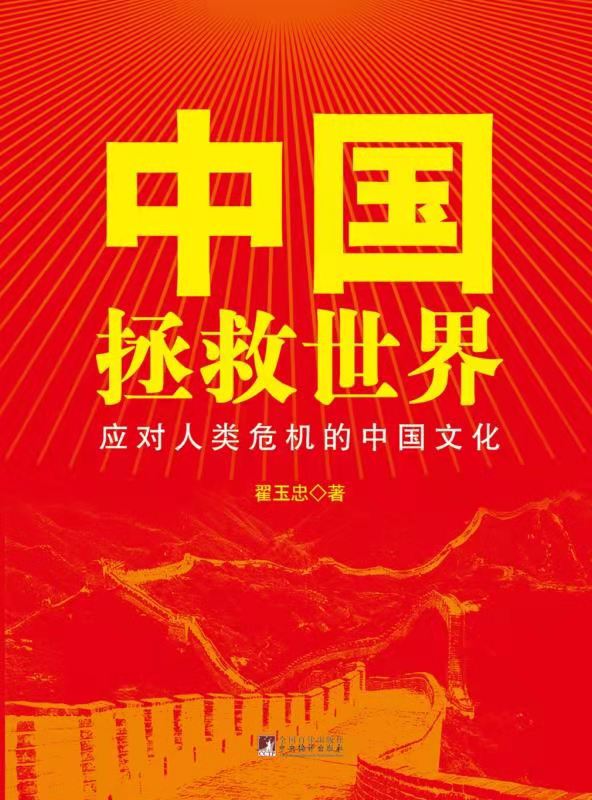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女士在研究《禹贡》时,就注意到“九州篇”的视角凌驾诸文化区系之上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心区域是以河南、关中(可能还有晋南)为中心的中央王朝,那是三代王畿之所在。
王畿文明先进,力量强大,否则不足以支撑中央王朝的存在。同时在王畿的周围,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方国。《战国策· 齐策四》记载:“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也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面对同一连续大陆上如此多的潜在竞争对手,决定了中央王朝不可能通过殖民手段一统天下,只能采取不同文化自然融合的形式,最终形成强大的文明有机体。 今天,当我们观察中国地图的时候,还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是从《禹贡》上载明的 “中心区域”平均散布开来的。换言之,从这一文明心脏地区到中国东南西北四方的距离大致是相等。 与西方主流均势理论注重实力和利益不同,东亚文明的扩展规律使先贤注重不同文化的异质共存(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有个专有名词“和”)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德”和“义”),现代西方外交中不变的利益原则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所唾弃。在外事领域,我们更注重大国与小国的互相帮助、和睦共处,并把战争看作迫不得已的行为。 《尚书·尧典》赞美尧的丰功伟绩时就说他能使“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就是说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变得友好和睦起来。这里“协和万邦”与21世纪“和谐世界”没有本质不同,尽管现代人已不清楚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为实现天下万邦的和谐,中国古典外交理论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学术方法。如同在政治经济学中先贤关注上与下、齐与非齐一样,在外交中,他们关注大与小,而没有同西方学术一样首先提出抽象的概念原则,再用这些概念原则演绎现实——无论演绎的结果与现实的差距有多大!
《逸周书·职方解第六十二》中指出,大凡邦国,大小都要互相维系。天子设置牧伯,凭其能力制定他们的职事,依其所产制定他们的贡物。文中说:“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 这种“大小相维”不是漂亮的外交辞令,而是现实政治的真实反映。《左传》中记有许多大国与小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案例。先贤认为,大国强国帮助弱小的国家符合国际行为规范——礼,是实现和平的保证,否则就是“非礼”。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子产总结说:大国到小国,应该表现出五种美德:赦免它的罪过,原谅它的失误,救助它的灾难,赞赏它的德行和刑法,教导它所想不到的地方,这样小国不困乏,顺服大国好像回家一样。《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灾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 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国。管仲建议齐桓公救邢。公元前659年齐桓公、宋桓公、曹昭公率领军队驻扎在聂北,诸侯联军救援邢国。邢军当时已经溃散,逃到了诸侯的军队里。诸侯联军最后赶走了狄人,装载了邢国的器物财货并让邢军拿回,各国军队没有私自占有。夏季,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诸侯替它筑城。《左传》强调:凡是诸侯领袖,救援患难、分担灾害、讨伐罪人,都是合乎礼的。《左传·僖公元年》上说:“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对他国的道义援助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体现在经济上。公元前717年冬天,京城派人来报告饥荒,鲁隐公就代为向宋、卫、齐、郑诸国请求购买谷物,这也符合普遍国际道义礼的行为。《左传·隐公六年》记载:“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春秋末年,《老子》将上述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哲理化了。《老子》用了整整一章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国要像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也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所以,有时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信任,有时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要保护小国,小国要协同大国,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应当以谦下为宜。《老子·六十一章》:“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谦下守雌的外事态度反映到军事就是以义用兵,讲究武德,将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老子》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六韬·文韬·兵道》说过类似的话:“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大小相维的国际观在战国已经极为成熟。《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的作者一方面抨击了当时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潮,另一方面指出了正义战争的必要性: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从未有废止战争的。战争由来相当久远了,它和人类一起产生。大凡战争,靠的是威势,而威势是力量的表现。具有威势和力量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从天那里来的,不是人力造成的。勇武的人不能使它改变,机巧的人不能使它移易……如果战争确实符合正义,用以诛杀暴君,拯救苦难的人民,那人民就欢迎,就像孝子见到了慈爱的父母,象饥饿的人见到了甘美的食物。人民呼喊着奔向它,像强弩射向深谷,像蓄积的大水冲垮堤坝。文中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外事理论总结为“外事武而义”(语出《逸周书·武纪解第六十八》),它是中华礼义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 当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赤裸裸的利益原则下大行霸权在时候,中国知识分子能否意识到人类还有更高尚的国际原则和建立于其上的世界秩序呢!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