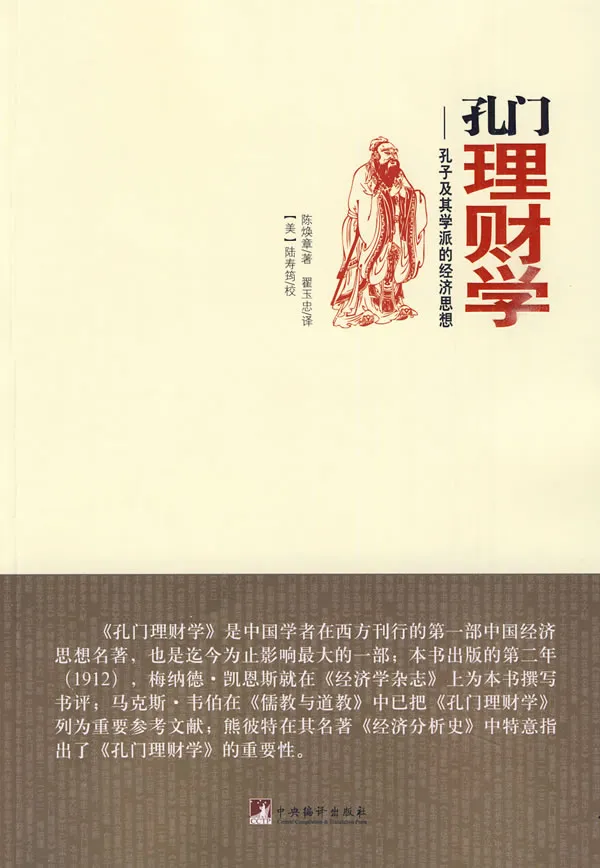关于财富生产的三要素,我们不妨从《大学》中选取下面一段: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这一原则本来应用于君主:如果一个君主拥有美德,就能统治人民,拥有土地,积累财富,(在这儿意味着资本),就会有许多东西可以享用。但这一原则也可以普遍地用于所有人。以商人为例。他必须首先拥有某种广义的德行,或曰长处,无论是体力上的、还是在智力上的、或是道德上的。如果竞争是完全自由的,他将获得与自己的长处成正比的财富。一个人如果一无长处,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显示出他的长处(例如有工作能力,却什么都不干),他将自外于人,不能靠自己获得任何财富。社会中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也不能长存。 游手好闲之人、寄生虫和小偷,尽管他们是坏人,但他们仍然具有某种可以取得财富的德行。因此,德行是根本,财富仅是它的结果。 于是,按照《大学》所言,生产的要素有三:第一是有某种德行的人,二是土地,三是资本。三个要素均属于生产的范畴。然后“使用”一词出现了,消费就跟着开始了。 将生产要素分为三部分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原则,它甚至能应用到原始生活中的单个人身上。首先,他自己必须是一个人;第二,他必须生活在某块土地上,利用土地捕鱼或打猎;第三,他必须有某种资本才能进行渔猎。在原始生活中,资本一定从属于土地,因为他可以没有资本而营生,但没有土地却完全不能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土地仅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有许多其他生产资料而不必拥有土地。因此,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要素:人和生产资料。但在孔子时代则不是这样。在井田制下每个人都接受一份土地,否则他就没有或极少生产资料。因此土地是一个独立的要素,在所有生产资料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和人造商品的区别非常突出,因为土地不是人工制造的,也不会败坏。《大学》将这三个要素分开来阐述是正确的。 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体,这一原则仍较为正确。国家财富的第一要素是人,第二是土地,第三是资本。不被占有的土地不能形成一个国家,除非它属于人。那些仅有可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人们也不能形成国家,除非他们拥有一些土地。可以存在这样的人们,他们有人力、有土地、有资本,却没有国家;但没有这样的国家,它既没有人、也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本。 按照《大学》中的的顺序我们将首先讨论人,然后是自然。换言之,我们将人置于土地之先。的确,土地不是人造的,甚至先于人类而存在。不过同样确实的是,土地之所以对人有用只是因为人参与了大地的生命,否则,这个世界只是一片荒野。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我们应首先关注人。而且,因为人类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发展,自然受着人类的摆布。所有的自然力只是像机器一样,帮助生产财富,而自然界的真正主宰是人类。因为上述理由,我们在讨论土地之前先讨论人。 这一先后次序对中国人产生了特殊的经济上的影响。中国为什么人口这样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拥有超出其养育能力的那么多孩子?为什么中国学者从不考虑如限制人口这样的理论?这是因为《大学》中说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按照这一原则,土地和资本都后于人。所有中国人都熟知这一原则,他们有谚语说:“钱是人挣的。”问侯的时候,第一个半句是“添丁”,第二个半句是“积财”。新年来到时,人们写的、说的都是“人财两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或整个国家如果人口增加了他们特别高兴,不仅因为更加热闹,也为了经济生产,因为他们认为人是主要生产要素。这无疑是由于《大学》的思想影响。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 - 1897,美国经济学家、現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说:“不是食物增长导致人口增长,而是人口的增长导致食物的增长。有更多的食物,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1】这在中国是常识。《大学》将人置于土地和资本之前,正是基于同样的理论。 杜佑(卒于1363 A.K. 或812 A.D.)在其《通典》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一开始,也列出这三个生产要素,他说: “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2】 他的论述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但这三样东西是所有经济生活所共有的。“地”和“人”不需要解释,“谷”一词是资本的主要代表,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因此,按照杜佑的观点,生产的要素也是三个——即资本、土地和人。他的顺序正好与《大学》的相反,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他用的是递进的顺序,而《大学》则反之。 注释: 【1】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P.97. 【2】《通典·食货一·田制上》。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