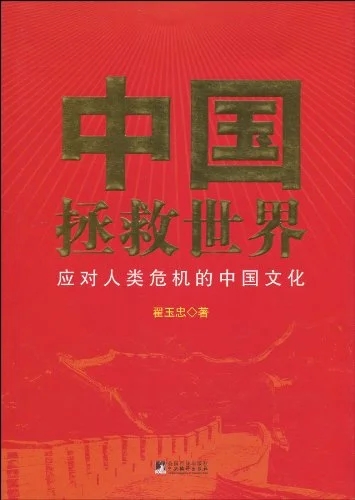中华礼义文明重兵尚武体现在社会制度上就是军民一体,寓兵于民的政策。 西周时期,战争频发,政府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都要以打猎的行式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称为“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大司马》条中讲得十分详尽。原文较长,我们只列出春蒐一节。上面说: “仲春,教[民众]习战。大司马用旗召集民众,整编队列阵形,如同实战时那样列阵。[教民众]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王执掌路鼓,诸侯执掌贲鼓,军将执掌晋鼓,师帅执掌提鼓,旅帅执掌鼙鼓,卒长执掌铙,两司马执掌铎,公司马执掌镯。教[民众]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快速、慢速,以及距离疏密的节度。接着进行春季田猎,有关官吏在立表处举行貉祭,警诫民众[不要违犯有关田猎之法],然后击鼓,于是开始围猎。[焚烧野草的]火停止燃烧,然后进献所猎获的兽以祭祀社神。”(原文: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师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 西周“田猎”军事演习只是军礼的一种,除了征伐之时,甚至兴办大型公共工程都属军礼,以提高民众的军事素质。《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条载“用军礼协同天下各国:大军出征之礼,是利用民众[的义勇];大校比以平均赋税之礼,是忧虑民众[的赋税不均];举行大田猎之礼,是为了检阅徒众[和战车];大兴劳役之礼,是为了任用民众[的劳动力];大规模勘定疆界之礼,是为了聚合民众。”(原文: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金文资料表明,《周礼》是追述西周政制的一部专著,关于寓兵于民的条目还很多(如地官司徒系统中的“乡师”条等等),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到春秋战争国时期,寓兵于民的政策已经极为完善,并为后世所仿效,最著名的就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和商鞅的“令民为什伍”(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管仲寓兵于民的政策在《国语·齐语》中记载甚详: “(管子作内政而寄军令)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是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xiāng chóu,亦作:相俦,意思是彼此在一起——笔者注),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 通过与西周制度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管子还是商鞅的寓兵于民政策,都是西周政治,王官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不是齐桓、管仲、秦孝公、商鞅这些先贤“大脑风暴”后的发明。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法家思想是中国古典国家学术——王官学的延伸。 武是国魂——军民一体的尚武精神在历史上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国魂。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推行保甲法以废除腐败的募兵制度,恢复中国传统的寓兵于民政策,人人习武,提高军队的战斗力。1072年,王安石在《上五事札子》写到:“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临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能够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尚武精神,甚至连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也怀疑寓兵于民的可能性,他质问王安石:“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宋史·卷一百九十二》)宋神宗死后,王安石变法很快成了明日黄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救中原王朝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全境占领的惨剧——不过中国尚武精神的消褪则比宋亡要早许多。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