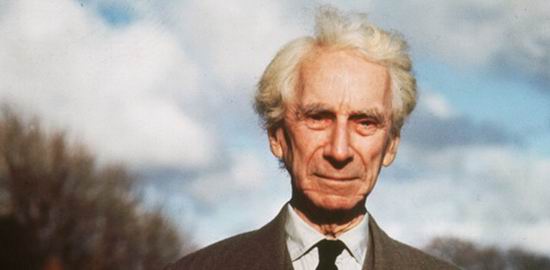人由于其脆弱性,不可能不生活在社会组织里,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分工。而过度的社会化,尤其是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存在,使个人的自由受到很大的压制,个人的选择空间变小,其尊严和需求被忽视。那么,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理想关系是什么呢?
人,独自生存是困难的,只能群居。群居,则不可避免地产生统治。
一方面,统治是必要的,否则,文明国家就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希望活下来,而且还要处于可怜的贫困状态。但在另一方面,有了统治,必然就有权力不平等的现象;权力最大的人就要不顾普通公民的欲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发展他们自身的欲望。因此,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是同样招致灾祸的;假如人们要求得到幸福,那就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得折衷的办法。
这个问题在民主国家里和在极权国家里当然是不相同的,在极权国家中,一切有关的组织都是政府的组织或部门,很少例外。
一切公私组织对个人的影响是从两方面发生的。有些组织旨在有利于个人实现他自己的愿望或实现被认为是他的利益;有些组织则旨在防止个人侵害别人的合法利益,两者间并无截然的区分。设置警察既为了防止盗窃,又为了增进良民的利益,只是警察对盗窃行为的打击远比为守法者的服务显著而已。关于这个区别,不久我将重新讨论;现在我们先来研究在文明社会里组织对个人一生所起的某种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之点。
首先从人的诞生说起。关于这件事,现在认为医生和助产士的服务是不可缺少的。从前认为毫无训练的甘普奶奶就足以胜任,现在则要求接生员必须具有公共主管机关所确定的一定技术水平。在整个幼儿期和儿童期,一个人的健康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国家的关注。不同的国家关心儿童健康的程度相当准确地反映在儿童和少年的死亡率上。如果父母骇人听闻地不尽父母的责任,当局可以把小孩从他们那里带走交给养父母或某个机关抚养。在五六岁时,小孩受到教育机关的照管,有好几年必须学习政府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知道的东西。大多数的情形是,在这一过程结束时,一个人的见解和思想习惯就终身确定了。
其中,民主国家中的儿童还受到非国家所加的其他影响。如果父母是笃信宗教的或从事政治的,他们就会把宗教的教义或政党的主张教给儿童。在孩子长大些的时候,他就会对一些有组织的娱乐越来越有兴趣,比如电影和足球赛。如果孩子有几分聪明但也不是很聪明的话,他也许受报刊的影响。假如他进的不是国立学校,他会养成在某些方面显得奇怪的看法(在英国,通常是认为自己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的看法)。同时,他接受适合于他自己年龄、阶级和民族的道德准则。 道德准则是重要的,但不容易解释明白。因为它包含三类没有明确区别的教训。 第一类是必须真正遵守、违者要受众人唾骂的;第二类是不可公开反对的;第三类是要求做到十全十美的,只有圣者才需要遵守的。适合于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主要是(虽然不尽是)宗教传统的结果,是通过宗教组织的活动起作用的,但在宗教组织衰落后还能继续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此外,还有职业上的道德准则:规定军官、医生或律师等等所不应作的事情。在现代,这类准则通常是各种职业团体订定的。它们是很有强制力的。例如教诲和军队对决斗的意见相抵触时,军官要奉行军队的意见;有关医疗和忏悔方面的保密甚至于法律相抵触。
青年男女一开始挣钱,各种组织就开始影响他或她的行为。雇主通常是一个组织;另外,很可能还有雇主们的联合会。工会和国家都控制着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除了像保险以及工厂法这类事情而外,国家还能用关税和政府法令来影响一个人所选定的行业的盛衰。一种工业的繁荣可以受到各种情况的影响,例如通货、国际性城市或日本的野心。
结婚以及对儿女的责任又使一个人和法律发生关系,并和主要来自教会的道德准则发生关系。假如他寿命很长,最后他可以享受一笔养老金;他的死亡还要经过司法部门和医疗部门的细心检查,以确定不是自杀或他杀。
有些事情有待于个人主动加以决定。假使女人愿意,一个男人可以和她结婚,求得幸福;在年轻的时候,他对于自己一生的谋生之计,很可能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在他财力所及的范围内,他可随意消遣他的空闲时间;假如他对宗教或政治有兴趣,他可加入任何一个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教派或政党。除了婚姻这件事,一个人即使在他有选择自由的时候,也仍然要依靠各种组织。除非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否则,他不能创设一种宗教,建立一个政党,组织一个足球俱乐部或自己酿酒喝。他所能做到的是在可供选择的许多现成事物中进行选择;但是竞争要在经济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把所有这些可供选择的事物尽可能弄得对人有吸引力量。
到目前为止,作为文明社会特征的各种组织的功效,同(比方说)较为不发达社会里的农民比起来,在于增加了个人的自由。你不妨把中国农民的一生对照西方工资劳动者的一生而加以研究。中国农村的孩子,固然无须乎上学,但从年岁很小的时候起,就不得不工作了。生活艰苦,缺少医药,他非常可能在幼年夭折。即使他活下去,他也不能选择其谋生之道,除非他准备当兵,做土匪或冒险迁移到大城市里去。风俗习惯剥夺了他的一切,只剩下关于结婚的一点极小的自由。他实际上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即使有,也没有赏心乐事来消遣。他经常生活在死亡边缘上,一遇饥荒,他一家很可能大部分人饥饿而死。男人的生活已经很苦,妻子和女儿的生活还要苦得多。在英国,即使是最下层的失业工人,他的一生和一般中国农民的一生比起来,几乎也是在天堂里了。
现在再谈另一类组织,即旨在防止一个人侵害别人利益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警察和刑法。就此类组织干涉的是诸如谋杀、抢劫和殴打之类的强暴罪行而论,它们增进(除了一小撮暴徒)一切人的自由和幸福。在警察管不到的地方,盗匪很快就造成恐怖的统治,匪帮以外的一切人不可能享受文明生活的大部分乐趣。当然也存在这种危险,即警察本身可能变成匪徒或者竟施行起某种形式的暴政。这种危险决不是虚构的,只不过对付这种危险的方法已为世人所熟知。另外还有一种危险,即警察可能为当权者所利用,来防止或阻挠对可取的改革予以支持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多少说明这样一个根本困难,即为了防止发生无政府状态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使现状在应该改革是更难得到改革。尽管有这种困难,文明社会里没有什么人认为有可能完全废除警察。
以上所述没有考虑到战争和革命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恐惧。战争与革命涉及国家自卫的本能,并引起对个人生活最严厉的控制。在欧洲大陆,几乎一切国家都普遍实行义务兵役。一旦战争爆发,各地方的各个适龄男子都可能被召去打仗,每个成年人都可能受命去做政府认为最有助于战胜的工作。凡认为其行动有助于敌人的人,都可能被处死刑。在和平时期,一切政府都采取步骤——有些更为激烈,有的不那么激烈——来确保公民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都乐意参加战斗,并在任何时候都忠于国家。政府在革命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随着革命爆发可能性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那么,在政府简直不关心公民幸福的地方,革命的危险性就大些。但是,像在极权国家里那样,政府不但独占人身强制权而且独占道德上和经济上的说服力,那么,这种政府在漠视公民方面能比权力不如它那么集中的政府走得更远。因为革命情感在那里不那么容易传播,革命也不那么容易发动。就国家不同于公民团体而言,可以预料:国家的权力越增加,它对公民的幸福就越不关心。
根据上面的简短评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组织的效能(除去由于政府自卫而产生的效能以外),基本上都是增进个人的幸福和安宁。教育、卫生、劳动生产率、积谷防荒等等,原则上都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事,这一切都依靠很高程度的组织工作。但是当我们谈到预防革命或预防战争失败的措施时,问题就不同了。无论人们认为这些措施怎样必不可少,它们都是使人不愉快的;要为这些措施辩解,只能根据一个理由,即革命或失败会使人更不愉快。这大约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可以说种痘、教育和筑路也都是人不愉快,但总不如天花、文盲和不可通行的沼泽地那么使人不愉快。不过,这种程度上的差别很大,差不多等于性质上的差别。况且,有关和平发展的各种措施,即使它们令人不愉快,为时也不一定很久。天花是能够消灭的,消灭以后,就无需种痘了。教育和筑路都可以用开明的方法是它们成为可以令人乐于接受的事。但是技术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使战争更令人痛苦,更有破坏性,并使以极权主义方法防治革命的措施更伤害人道和理智。
个人和各种族之间的关系另有一种分类法:个人可以是组织的顾客,可以是组织的自愿成员,可以是组织的非自愿成员,也可以是组织的敌人。
如果一个人是某些组织的顾客,他必然认为这些组织对他的生活舒适有帮助,但它们不能使他增添很多权力感。当然,他对这类组织的服务所抱的好感也可能是错的;他买的丸药可能不灵;啤酒可能是坏的;赛马会可能使他把钱输给以赛马赌博为业的人。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从他所光顾的组织那里得到一点东西——希望、娱乐和个人进取感。一个人有希望每一辆新车,这一希望是他有事可想,有话可谈。总的说来,自由选择如何花钱是快乐的一种来源——例如,喜爱自己的家具就是一种很强烈的、很普遍的感情,如果国家供给我们大家备有家具的房间,这种感情就不存在了。
由各人自愿组成的组织包括政党、教会、俱乐部、联谊会、自愿投资者组成的企业等,其中有许多是和同种的其他一些组织处于敌对地位的,例如对立的政党、不同派别的教会以及竞争的商业企业等等。因敌对而产生的争夺是对争夺感兴趣的人有了一种戏剧感,并使他们权力欲的冲动找到了出口。除非国家的力量薄弱,这种争夺是限制在法定范围之内的。法律对于暴行或严重的欺诈行为是要处罚的,除非执法者是秘密同谋者。对立组织之间的斗争,为当局所迫而采取不流血的形式时,总的看来,是为好争斗和爱权力之类的感情提供了有用的出口。否则,这些感情很可能要寻求更凶险的方式以求满足。假使政府办事松懈或者不公平,政治上的争夺就有堕落为暴动、暗杀和内战的危险。但如这种危险已经避开,政治争夺就是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有益因素了。
由各人非自愿组成的最重要的组织是国家。不过,自盛行国籍主义以来,国家成员的资格,虽非出于公民的志愿,但通常却符合他的志愿。
他本来也许可以成为俄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普鲁士人,或者也许意大利人,但不管这一切诱惑,诱使他归属别的国家,他依然还是英国人。
大多数人即或有改换国籍的机会也不会这样做,除非他们的国家作为外国人的代理人。在加强国家的力量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国籍主义的胜利更有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资格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一个人对于国家的忠诚往往超过他对于自愿参加的组织(例如教会和政党)的忠诚。
对国家的忠诚既有积极的动机也有消极的动机。忠于国家是和热爱家庭和家族有联系的。但如没有增添喜爱权利和害怕外国侵略者一对孪生动机,热爱家庭和家族就不会和忠于国家相结合。
国家间的争夺不同于政党间的争夺,前者是全民的。林白的一个孩子被绑遇害震动了整个文明世界,但是这样的杀人行为,将以更大的规模在下一次战争中成为常事,而这所谓下一次战争正是我们大家都在准备着的,以英国说,它每年耗费我们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没有别的组织能鼓起什么东西赶得上民族国家所激发起来的对国家的忠诚:国家的主要活动是为大规模杀人做准备。正是对于这个制造死亡的组织所抱的忠心才能使人们忍受极权政府的统治,并宁愿冒着毁掉家庭、儿女以及我们全部文明的危险,而不肯屈服于外国的统治。个人心理和统治组织已经形成悲剧性的结合;假如我们仍然没有力量寻找一条不经历灾难的出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一定要为这个结合而受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