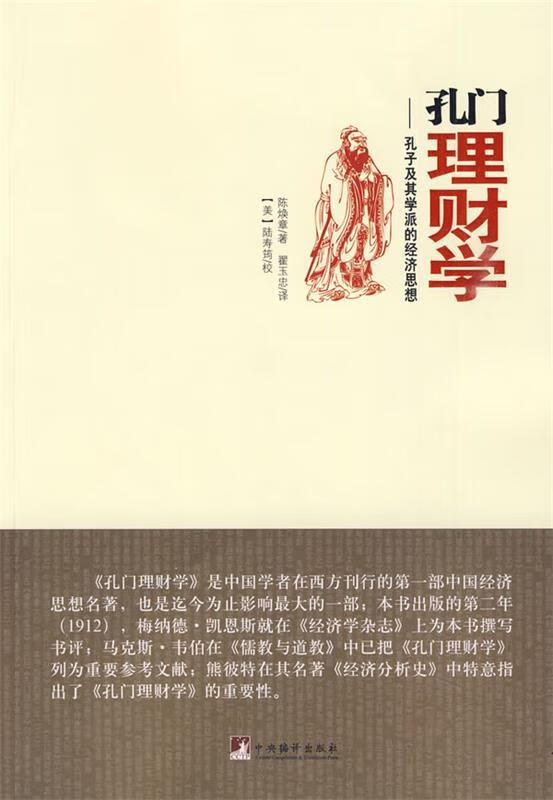较之于生产问题,儒家的经济理论更多地注重分配,因为儒家有较多的社会主义性质,较少个人主义性质。关于财富分配有很多原则,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类,即平等、生产力和需求。 (一)按平等原则分配 首先,财富应平等分配。平等分配不是说每个人应有同样多的收入,而是每个人都应有同等机会去取得同样多的收入。因此,确有少数人凭其能力和贡献公平地得到较多的财富,但只要多数人有平等的生产机会和符合社会标准的生活水平,不至陷于贫困,这就是平等分配。事实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平等,只有大致的平等。 荀子说: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 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1】 按照孔子的社会原则,有两类人,一类是地位尊贵者,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另一种是地位卑贱者,如庶人。贵人阶层当富有,庶人阶层当贫穷,因此“富”和“贵”一词相联,“贫”和“贱”相联。但没有什么能将任何人固定于某一个阶层,每个人将按自己的能力有上有下。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这五个阶层之间,没有财富上的平等。但在数量最多的庶人中,财富必须平等分配。一方面,他们中无人具有更多的、可以增加财富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不准上层阶级从事任何可以同庶人竞争的、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平等分配。 我们必须懂得,按照孔子的原则,贵贱两个阶层不应有巨大的鸿沟。他们只是相对富有和贫穷,他们不应有太多的差别。在周代曾经存在阶级斗争,这表现在《诗经》中,上面说:“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2】 这前四句描写卑劣的朝廷宠臣们的财富和享乐,最后两句是作者在想到社会的混乱和正在到来的毁灭时的忧伤。下面继续说:“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3】 这首诗写于幽王统治时期(230~220 B.K.或781~771 B.C.),是他毁掉了西周。该诗说明当时存在着巨大的贫富鸿沟。如此不平等的分配是灭亡的征兆,孔子以此作为对后代的警告。因此《尚书》中说:“昔君文武丕平。”【4】孔子提倡财富平等分配的理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来的。按照人类本性,有太多财富的人一如有太少财富的人一样糟糕。孔子说: “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5】 因此,平等分配是为了使穷人和富人都保持良好的本性,保障社会太平。简而言之,孔子的意思是,政府是财富的分配者,是生产和消费的掌控者。 在《春秋繁露》“度制”一章中,董仲舒说: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6】 这是对孔子原则的解释。 平等是孔子的一大原则,它还有其世界性。因此,他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倡此原则的。《大学》最后和最长的一章题为“平天下”,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理财。在《中庸》中,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可见,孔子设想的平等分配是要用之于全天下的。 在孔子时代,各国诸侯和贵族为了扩展领土和增加人口而相互战争,因为他们认为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会使他们更富有。但这些战争不仅无益于人民,还会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当季氏要攻击鲁的属国颛臾时,孔子提出了伟大的平等原则。他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7】 这三个特点,均、和、安是孔子经济理论的目的。但和、安是平的结果。因此,财富的平等是基础。 (二)按生产力分配 第二,应按生产力分配。孔子说: “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易》曰:‘不耕获,不菑畲,凶。’”【8】 所以,孔子为儒生们制定了一个原则:“先劳而后禄”。《礼记·儒行第四十一》按照孔子的原则,分配必须与生产的结果相一致。即使很难确定生产力的精确数字,这一原则本身仍是公正的。待我们考察工资问题时再进一步讨论。 (三)按需分配 第三,应按需分配。这是《春秋》的一个重要原则。《春秋·隱公元年》记载:“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这一礼物本不是鲁国的东西,而是天子给的,为何孔子用“归”一词呢?那是因为他想说明接受者隐公应与天子共同拥有这些东西。何休解释这一原则如下:“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无当相通。”【9】这像共产主义思想。但我们必须更清楚地理解它。孔子承认财富的私有权,但他不赞成拥有者享有绝对的权力。因此,他让社会作为所有东西的最高拥有者,暂时拥有者只是受托人。既然自然界也是生产过程的合作参与者,没有人能凭着占有理论或劳动理论宣称对任何东西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所以,财富的分配就应该根据社会成员的需要。简而言之,拥有较多财富的人有责任与人分享,没有任何财富的人有权利接受分享。这是《春秋》的原则,上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虽然那并不说明隐公没有财富。 《论语》中孔子说:“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10】这是他关于分配的总原则。 孟子也清楚地解释了按需分配的理由。他对齐宣王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1】 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井田制中可以得到解释。在他对宣王提出上述谏议后,他马上简单描述了该制度。的确,足以让人成为善民,这才是公正分配的依据。如果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除了极少的例外,无人能充分发展他的智力和道德。【12】 注释: 【1】《荀子·荣辱第四》,意为:高贵得做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欲望,那么从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从物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他们,使他们有高贵与低贱的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这就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那么农民就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在种地上,商人就把自己的精明全都用在理财上,各种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器械上,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这种情况叫做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门、招待旅客、守卫关卡、巡逻打更,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所以说:“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这就叫做人的伦常关系。《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庇护各国安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2】《诗经·小雅·正月》,意为:他有美酒醇又香,山珍海味任品尝。四邻五党多融洽,姻亲裙带联结广。想我孤独只一身,郁郁不乐心忧伤。 【3】《诗经·小雅·正月》,意为:卑鄙小人居好屋,庸劣之徒享米禄。今世黎民太不幸,老天降灾伤无辜。富贵人家多欢乐,可怜这里却孤独。 【4】《尚书·顾命》,意为:先君文王、武王很公平。 【5】《礼记·坊记第三十》,意为:小人贫则穷困,富则骄横;贫困了就会去偷盗,骄横了就会去乱来。所谓礼,就是顺应人的这种情况而为之制定控制的标准,以作为防止百姓越轨的堤防。所以,圣人制定出一套富贵贫贱的标准,使富起来的百姓不足以骄横,贫下去的百姓不至于穷困,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至于对上级不满,所以犯上作乱的事就日趋减少。 【6】《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 【7】《论语·季氏篇第十六》,意为:我听说,对于诸侯和大夫,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于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 【8】《礼记·坊记第三十》,意为:相见之礼,是在行过相见之礼以后才奉上见面的礼物。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要教育百姓先做事情而后接受俸禄。……《易经》上说:“不耕而获,不开荒而得到良田,凶。”)。 【9】《春秋公羊传注疏·隱公元年》。 【10】《论语·雍也篇第六》意为:我听说过,君子只是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是周济富人的人。 【11】《孟子·梁惠王上》,意为: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恒心的,只有士能做到。若是民众,没有固定的产业就因而没有了恒心。一旦没有恒心,就会放荡胡来,无所不为。等到陷入罪网,然后跟着惩治他们,这是欺罔民众。哪有仁人当政而可以做欺罔民众的事呢?因此,贤明的君主规定民众的产业,必须使之上足以事奉父母,下足以蓄养妻儿,丰年能够温饱,荒年可免于死亡,然后驱使他们向善,所以民众容易听从。现在为民众所规定的产业,上不足以事奉父母,下不足以蓄养妻儿,丰年劳苦艰辛,荒年不免于死亡。这样,仅仅救济死亡都恐怕来不及,那还有余暇讲求礼义呢? 【12】理雅各教授(Prof. James Legge)评论道:“好的政府应关注和表现为人民物质上的幸福,他的这一原则值得给予所有的荣耀……当孟子教导说对于过着贫困悲苦生活的民众进行教育很少成功时,表现出他对人性十分了解。现在教育学家们似乎普遍承认这一点,但我认为在欧洲只是在近一个世纪,人们才像两千年前中国孟子那样将此看得那么确定和重要。” Chinese Classics,vol.ii.pp.49~50.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