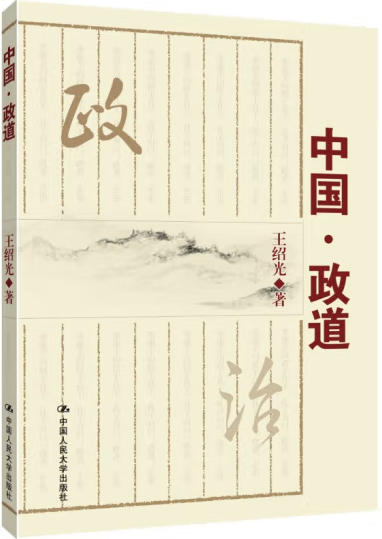与西方思想家一样,中国历代思想家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理想政治秩序。在中国谈到理想政治秩序,就不能不提到老子、孔子、孟子、墨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不错,直到大约100年前,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探求理想政治秩序时全然没有使用过“政体”这个概念。[36]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探求毫无价值。有人把中国古代政治学贬低为“研究(国家统治者的)统治术的学问”,似乎除了“在维护国家君主最高统治权力之下”的“治吏驭民术”,中国思想家别无建树。[37]还有人把丰富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简单化约为“以如何帮助君主得天下、坐天下为旨归,以‘成王败寇’的后果论作为判断标准……中国政治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公共利益的维度”[38]。这是典型的“一叶蔽目,不见太山”。 如果政体不是中国思想家的切入点,那么他们的切入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治国理政之“道”。诸子中无论哪一位,没有人不谈“道”。“道”就是中国思想家探求理想政治秩序的关键词。[39]而“道”与西语中的politeia一样,又恰恰是中文中最难理解、歧义最多的一个字。“道”的原义是供人行走的道路,引申开来有几十种意思。如果仔细梳理的话,这其中与治国理政相关的意思大概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事物的本体及其规律。道路是看得见的“道”,但还有看不见的“道”。《老子》的说法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韩非子·解老》则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吕坤将他们的说法概括为,“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呻吟语·谈道》)。 这个意义上的“道”的本体、主旨可以被叫作“道体”。按清代陈确《答唯问》的说法,“道体本无穷尽,故须臾不可忘戒惧”。[40] “道”的内在规律被叫作“道理”,无论是权力多大的人(包括君王、皇帝)都不可违抗,“无权不可为之势,而不循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功”(《文子·自然》)。荀子把“道”的重要性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王霸》);“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荀子·君道》)。商鞅的说法更直白:“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商君书·错法》)。“道”听起来很神秘,但在有些人看来其实质非常简单;正因为简单,“道”的实现才非常不容易,“尧、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个天然自有之中行将去,不惊人,不苦人,所以难及”(《呻吟语·谈道》)。 从无所不包的“道”还可以引申出各种事物的特有之道,如《易·说卦》所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如果说治国理政有一种“道”的话,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政道”,而“政道”就是“正道”。[41]在《礼记·哀公问》中有一段记载:“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这里,孔子不仅断言“人道政为大”,而且指出“政者,正也”。这与《论语·颜渊》中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使带强烈法家色彩的管子也同意这个看法:“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管子·法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概念意味着只有“正”才能“治”。[42] 上面引用的《礼记·哀公问》接下来是,“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这就是说,按照中国思想家的理解,在政治领域,所有主体,从每位普通百姓到处于权力顶端的帝王,都有其处事之道。《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陆象山说得更具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43]。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人伦即是政治,人道因此是治国理政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外,在理想社会里,更重要的是,当官要有当官的样子,尤其是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中国古代典籍充满了关于君、臣之道的讨论,《荀子》有“君道”、“臣道”;刘向的《说苑》第一篇就是“君道”;《贾谊新书》有“君道”;葛洪《抱朴子外篇》有“君道”;道家名著《亢仓子》有“政道”、“君道”、“臣道”、“贤道”、“兵道”等篇;《贞观政要》开篇也是“君道”;吕坤在《呻吟语·治道》中则从“天之道”、“圣人之道”、“圣王之道”、“为君之道”、“为政之道”、“宰相之道”、“御众之道”一直谈到“(修己)立身之道”、“齐家之道”、“百姓之道”。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一方面可以从“上下有序”的角度理解;另一方面,既然有“君君”之说,就意味着君主必须遵循思想家为他们设定的“君道”,不得胡作非为。例如,与历代先贤一样,吕坤在《呻吟语·治道》中特别提醒君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与《贞观政要·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思想一脉相承。 还有一些古代典籍虽然没专设“君道”篇,甚至没有使用“君道”这个词,但也大谈特谈“君道”,如《吕氏春秋》,其“贵公”篇实际讲的就是“君道”: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再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虽然对现实中的人君深恶痛绝,斥责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但也提出了自己的君道观,即“天下为主,君为客”[44]。 萧公权说,“二千余年之政论,大体以君道为中心”,大体是不错的。[45]但是,君道论的重点不是鼓励君主滥权枉法,而是在充分肯定君权至上的前提下,用“立君为民”的“君道”理想来约束乃至限制君权,来抨击昏君、暴君。自先秦以来,历代都有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君主政治的种种弊端;所谓著名思想家,几乎都曾试图匡正时君,而不是取媚时君。因此,钱穆认为,儒家的终极政治理论与其说是助长君权,毋宁说是限制君权。[46] 进一步,“道”还有层次,如《礼记·大学》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的“道”就是“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或反过来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按《礼记·大学》的说法,这叫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道”的最主要的方面可以被叫作“道要”,如《管子·任法》:“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垂拱而天下治”;也可以被叫作“道基”,如唐代李善在注释《文选》时引《庄子》说,“无为无治,谓之道基”;还可以被叫作“道根”,如汉代荀悦的《申鉴·政体》说,“恕者,仁之术也;正者,又之要也。至哉,此谓道根!” 当然,对于“道体”、“道理”、“道要”、“道基”、“道根”的内涵,对于如何践行君、臣、父、子之道,对于怎样“修、齐、治、平”,不同思想流派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还相互对立,恰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如何分政体、如何评价政体众说纷纭一样。 第二,道德、道义,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德性”、“正义”,《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里的“道”便是指道义。《淮南子·氾论训》说“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意思也差不多。贾谊在《新书》中把“道”与“德”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这里,贾谊不仅指出“道者德之本也”,同时也列举了“德”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之所以非常强调“德”及其相关的教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同样的制度,尧舜用之则治,桀纣任之则乱。 关于第二层意义上的“道”具体有哪些内容,不同的思想家在不同的场合说法未必完全一致。孔子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其他儒家学者往往以仁义作为行为准则和规范,如东汉荀悦在《申鉴·政体》中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后汉书·种岱传》把仁义与道德画上等号:“仁义兴则道德昌,道德昌则政化明,政化明而万姓宁”。韩愈在《原道》中表达的看法也大同小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墨子强调的重点则不太一样,按他的说法,“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 陈来指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正义’被所有政治思想家视为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石或基本属性,以‘正义’涵盖所有的政治美德。而在中国古史时代,则以‘德’(后来更以‘仁’)来涵盖中国古文化所肯定的一切政治美德。在西周以来逐步发展了一种思想,即认为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之后还有一个道德法,政治运行必须合于某些道德要求,否则就必然导致失败”。这个概括是十分有见地的。陈来同时指出,“在君主制下,政治道德当然首先是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行和规范。君主的个人品德在政治实践中展现为政治道德。周人明确认识到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政治的道德性格对维持政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47]。其实,何止是周人,后来历朝历代的思想家都会用直率或委婉的话语来告诫君主:治国理政的最终目的是为天下苍生谋利益,而不是为了君主个人及其皇亲国戚的一己私利。这岂是“研究统治术的学问”所能解释的。 第三,治理及其方法、技艺、途径。“道”与“导”同。《论语·学而》有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何晏《集解》引包咸曰:“道,治也”。当《商君书·更法》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时,其意思便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汉书·董仲舒传》中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也是指治理天下的途径。 治国当然需要有一套规矩,《孟子·离娄上》曰,“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朱熹的解释是,“道,义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孟子集注》)。商鞅的说法更简洁:“王道有绳”(《商君书·开塞》)。治国还需要有一套政策、方法、措施,往往被称为“道术”、“治道”、“治术”。 孔子的说法众所周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孟子的观点与孔子略有不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墨子则用下面这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治道:“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中》)。“兼”为何如此重要呢?墨子把话题再次说到“道”上:“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兼爱下》)。 商鞅的看法与墨子不同,他强调的是“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轴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商君书·定分》)。 庄子不同意上面提到的所有看法:“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外篇·在宥》)。 到了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程颐在为皇太子讲解《尚书·尧典》时,“帝王之道”就变成了“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48]。程颢、程颐还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49] 具有丰富从政经验且勤于思考的明代思想家吕坤谈到“治道”时感触特别多,他下面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对治国理政颇有启发意义: “圣王同民心而出治道”。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 “人君者,天下之所依以欣戚者也。一念怠荒,则四海必有废弛之事,一念纵逸,则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故常一日之间,几运心思于四海,而天下尚有君门万里之叹。苟不察群情之向背,而惟己欲之是恣,呜呼!可惧也。” “任人不任法,此惟尧、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而任人,未有不乱者。” “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万政举;百姓不足,万政废”。 梁漱溟在评论《呻吟语·治道》时指出,“这是心得,不是空话。虽出于一人之笔,却代表一般意见”[50]。 注释: [36] 这倒不是说“政体”二字从未出现在中文典籍中,但中文典籍中的“政体”指为政的要领,而不是指政权的形式。见汉代荀悦的《申鉴·政体》、唐代昊兢的《贞观政要·论政体》等。即使运用西式政体思维方式,中国历史上也未必只有一种政体。阎步克指出,“梁启超的‘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之说,是一个宽泛的说法。梁氏并不认为中国古今政体一贯,相反,他把中国专制政治分为若干进化阶段,给予了卓越的讨论,这是前无古人的。这个“惟一政体,是经历了演化的,它有一个历史的维度”(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148 页)。如果考察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盯着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中国历史上的政体绝不是“君主专制”可以概括的。分封制下的君主制与郡县制下的君主制不一样;受世袭贵族、宰相、官僚体系掣肘的君主制与不受任何掣肘的君主制不一样。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西周的国家称为“封建帝国”,与秦朝以下的“统一政府”加以区别。他又将汉初称为“平民政权”,以凸显与秦以前的“贵族政权”及西汉中叶以后的“士人政府”的不同。他还将明代政治称为“君主独裁”,清代的称为“狭义的部族政权”。[参见阎鸿中:《职分与制度:钱宾四与中国政治史研究》,载《台大历史学报》,2006 (38),112页。]实际上,只有在古希腊或中世纪规模很小的城邦才可能(只是可能而已)产生比较纯粹的政体。随着政治实体规模的扩大、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进行。几乎所有政治体制都是混合政体,而且混合的方式五花八门,使得政体分析难以进行。 [37] 参见郑传坤:《中西古代政治学特点的比较及其借鉴价值》,载《政治学研究》,2001(4),23 页。 [38] 郑戈:《千年政体论,今朝是与非》,载《南风窗》,2012 (11)。 [39] 参见徐大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载《政治学研究》,2004(3),26页;葛荃:《论传统中国“道”的宰制——兼及“循道”政治思维定式》,载《政治学研究》,2011(1),55页。 [40] 萧公权概括说,“儒家贵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法家以君主为政治之本体”。[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179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1] 古代典籍中的“政道”二字的使用是指施政的方略。 [42] 参见陈赟:《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的政道与治道》,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2~17页。 [43] 转引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46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4]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也有类似“君道”的讨论,例如,在《论君主政治》中,阿奎那一方面论证“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另一方面用很大的篇幅讨论“有德之君”(与暴君、与昏君对立)必须具备的“德性”与“能力”。有意思的是,阿奎那的中译者借用了不少来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概念,如“仁政”、“有道”、“无道”,来翻译阿奎那的著作。(参见马清槐译:《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实际上,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直至近世,西方一直存在一种被称为“君鉴”(拉丁文原文为 specula principum,或直译“君主之镜”)的文献,其针对的对象是国王、皇帝及王储,讨论他们应该遵循的原则、道德、修养、责任、规矩和处事方式。参见 Lester Kruger Born,“The Perfect Prince:A Study in Thirteenth-and Fourteenth-Century Ideals,”Speculum, Vol. 3, No. 4 (Oct. , 1928), pp. 470 - 504; Lester Kruger Born,“The Perfect Prince According to the Latin Panegyrist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55, No. 1 (1934), pp.20 - 35; Michael P. Mezzatesta, "Marcus Aurelius, Fray Antonio de Guevara, and the Ideal of the Perfect Pri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Art Bulletin, Vol. 66, No. 4 (Dec. , 1984), pp. 620- 633。 [45] 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825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6] 这是余英时对钱穆的解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50~51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 [47]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29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 [48]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二《尧典》,见《二程集》, 10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9]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见《二程集》,531 页。 [5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40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王绍光,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摘自《中国·政道》,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