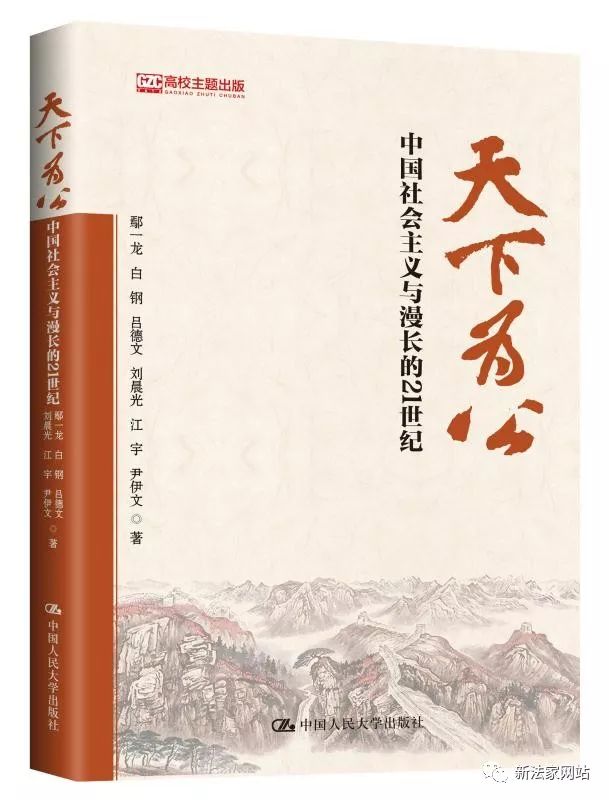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的经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新路。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好的金融。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能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第一,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大部分流入了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实向虚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也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会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的条件,不能像美国一样让全球为其分担后果。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战略腾挪空间,不必走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老路,应自觉引导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向国外转移,同时,推动国内制造业与国外制造业联动发展,拓展制造业发展的全球空间。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世界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同时也拓展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拓展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强实的同时还需要抑虚。一切实物资产只要具有流动性,理论上都可以金融化,而金融衍生品泛滥的前提就是实物资产的过度金融化。农村土地等实物资产不宜过度金融化,应该最大化其使用价值,而不是炒作其金融价值。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金融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使得金融市场成为一种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就告诫说,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要很高,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中国股市被调侃为“毫无门槛的赌场”,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几十年下来的结果很清楚。股市就是信息、资源高度不对称的战场,越是弱势群体,越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掠夺的对象,许多股民都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导致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如何从别人口袋里圈钱的“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层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能够重建群体共担风险、群体共享收益的新共同体,其不同于传统的共同体,是个体自由选择的共同体。 罗伯特·席勒提出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他说的大规模的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这又使得风险扩散与放大变得更加容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在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有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第三,国家统筹金融资源,打造居民与国家的金融利益共同体。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必须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会造成洪灾。近年来,随着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减少,其吸纳金融资本的能力不断减弱;企业、居民积聚的财富增加,资本供给的压力不断加大,再加上国际游资在其中游弋出击,使得经济运行发生波动,一阵儿是股市暴涨暴跌,一阵儿是楼市的暴涨。其背后就是这种寻找出口的流动性力量在兴风作浪。

治理的方法必须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主要靠疏导。国家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的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并存,这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巨量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发展中去。 我国仍然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等领域是投资不足的,之所以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收益排他性模糊。 史正富还提出,可以通过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相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解决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第四,避免住房等资产过度金融化,使其回归使用价值属性。 住房是民生品,不是普通商品,更不是金融产品。住房金融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市场出现空前的非理性繁荣,2006—2015年10年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176亿平方米,相当于每户竣工了近44平方米。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难分伯仲,但与此同时,许多民众却“望楼兴叹”——买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剧财富所有者与劳动阶层之间的分化。居民财富中,住房是大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法国与英国两国的财富与收入比自1970年以来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财富比重的急剧上升。中国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中国居民财富的六成左右是房产净值。 这使得社会分化为炒房阶层、自住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炒房阶层就是所谓的“投机资本家”,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空手套利;对于自住房阶层,住房对他们的意义还是使用价值,而不是金融价值,房价高低无关紧要。 一线城市的底层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无房阶级”。当一座城市的房价上涨到依靠劳动收入(无论多高的薪水)无法购买的时候,房价就已经成为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阶层与劳动者阶层划分的天然界限,并可能摧毁劳动者阶层通过奋斗和诚实劳动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住房是民生之需,只有实现一个家庭基本上有一套房的保障,才能让老百姓有安定的生活,社会才会稳定。对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要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民生。只有少部分所谓“精英”可以不顾民生,只要幻想的“民主”。 如何控制房价?光靠以限价为主的政策显然作用不大。调控的历史也表明,越是严厉的调控越是带来下一轮的报复性快速增长。治本之策就是要落实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改变住房的投机品属性,回归商品和民生品的属性。 其一,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任何资产都可以金融化,流动性越高,金融化的能力越强;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动性,增加住房资产变现的难度。 可以通过限售而不是限购来遏制频繁交易。例如在2017年的这一轮调控中,有的地方规定购买的住房若干年之内不能交易。这种降低住房资产流动性的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加大持有投机房产的成本。征收房产税,有助于加大持有房产的成本,特别是对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进税率征收。 要严控住房贷款的杠杆率。对于二套房提高首付比例,对于三套房以上必须全款购买。 其二,供需总量平衡的调控。进行总量平衡调控,使得土地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大体保持平衡,就不会造成一房难求的状况。而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的方法,可谓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调控方式的一种动机可能是为了炒地皮。即便不是如此,也反映了某些城市的“乱计划”思维,不是根据需求来计划供给,而是在控制人口的一厢情愿的思维下控制住房用地的供给,结果不但人口没能控制住,而且住房用地也出现了严重的供需失衡,导致短短十几年间住房价格暴涨了十多倍,可谓政府庸政、怠政的典型。 真正的供需平衡的计划,是根据需求变化来逐步增加土地供给。比如,根据每年住房刚需以及改善性需求增加量,有序增加土地供给,以避免因为供需失衡,出现炒作地价、炒作房价的问题。对于市场需求变化这些简单的算术题,通过经验性估算就可以得出,更别说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了。不是能不能为的问题,而是愿不愿为的问题。 在根本上,政府需要管住自己炒地皮的冲动。高明的“土地财政”不是卖地,而是像重庆等地那样为了公共利益运营土地,先实施土地收储政策,再逐步开放给开发商,利用土地未来的收益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使得土地的涨价收益落入公共财政的口袋,而不是落入私人开发商和炒房集团的口袋。这才是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土地运营方式。 同时,要通过政府的平准机制,抑制住房价格的暴涨,改变房价单向上涨的预期,让炒房者血本无归,让乱炒地皮的企业血本无归。 其三,要大力推行租赁转“共有产权”的住房制度。 如果说股市上涨的时候是贪婪,下跌的时候是恐惧,房市则是炒房者的贪婪与刚需群体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暴涨。 租赁转“共有产权”的住房制度根本上就在于服务刚需。租房的青年人既是房客,又是未来的房主。政府牵头建设大批政策房,由政府供地,地价便宜,主要是建造成本,并由政府回购,规模要达到市场占有的1/3以上。政府将房子租赁给刚需群体,在租赁期间可以实施“租购同权”,租赁者与购房群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达到若干年限以后,租赁者可以申请按照“共有产权”购买,购房者可以终身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自由交易。“共有产权”实质是限制住房的投机品属性,而充分保障其民生品属性。 第五,政府设立金融市场平准机制。 金融市场本质上是非均衡的。由于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拆借,金融的风险很容易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一旦触发危机,就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只有政府予以强有力干预,强有力地执行去过度杠杆化政策,才能避免暴涨暴跌和系统性危机。 好的金融市场不应该鼓励暴利,需要有相应的政府平准机制,抑制波动,露头就打,避免资金恶意炒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同志领导的稳定财经的战役就是对平准机制的成功应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城市发生了通货膨胀,市场投机活动极其严重。为了打压市场投机活动、稳定财经,陈云同志领导了一场经济战,从商业、银行、财政、税收等方面四路出兵。商业上,由政府逐步抛售商人囤积的物品,使市场物价不涨反跌;同时,银行贷款限制借出数目,少投放票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去杠杆”。几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当综合力量超过商人的力量的时候,商人就会跟着政府调控的意图走,从而平稳了物价。 当下和未来,党和政府如何驾驭金融资本?这段历史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营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海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类似当年稳定财经的办法,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力量,与资本家的投机行为抗衡。投机资本家力量分散,而国家力量统一,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则战无不胜。 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英国则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发动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成立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国际金融大鳄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作者鄢一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2018-07-04 摘录于《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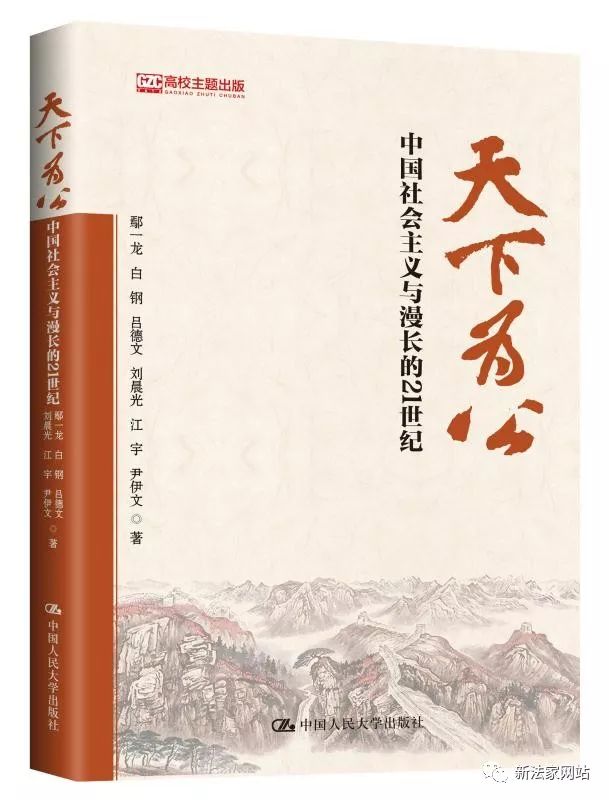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