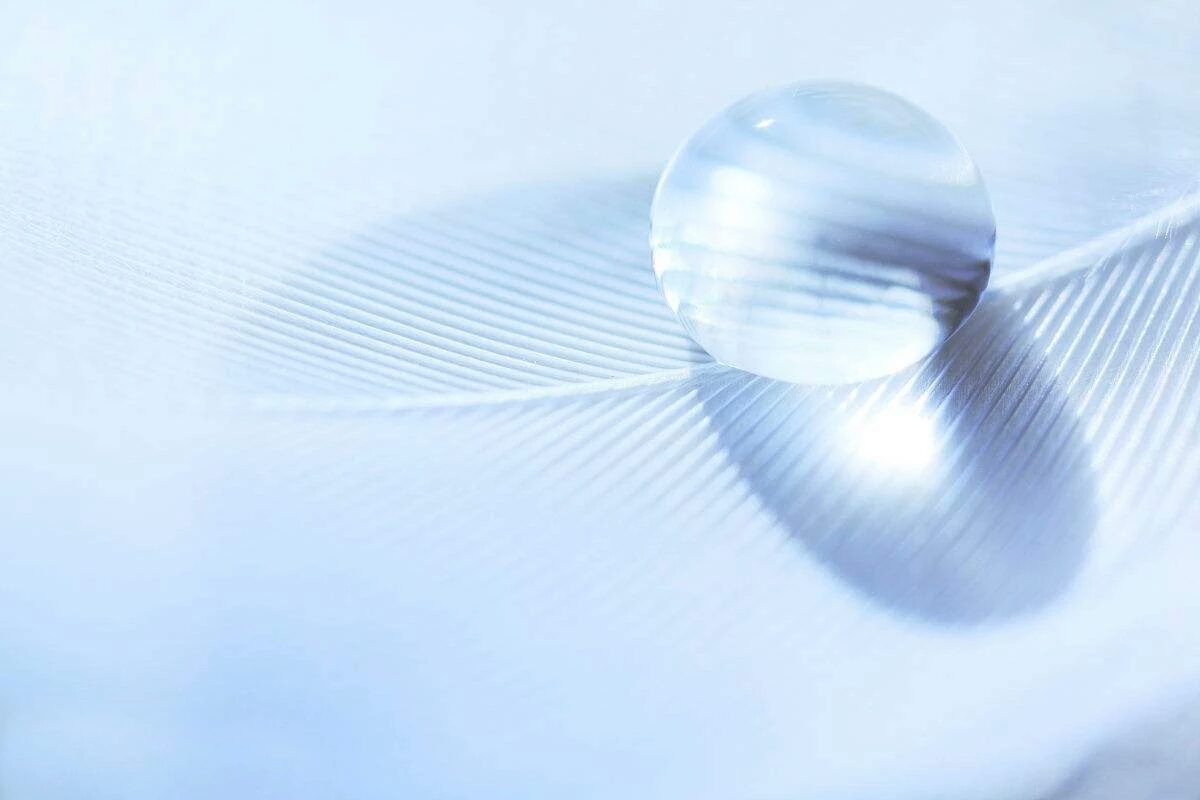【摘要】想要理解杨朱的思想,必须首先明了这个一个事实,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杨朱的学说,正是基于此而提出的一种纠正思路。就思想深度而言,杨朱的学说并无多大意味;因此写作本文,只是为了了结流传的两千年的谬见而已。 一、引言 杨朱,又称杨子、阳子居、阳韩生 战國魏國人,其史料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及《吕氏春秋》等书,仅寥寥数语,而《列子-杨朱篇》并不可靠。 由于孟轲把杨朱与墨子并列为主要论敌,于是人们常常以为,杨朱的理论与墨子的理论、特别是兼爱说截然相反,本文的论述将表明,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杨朱的学说简单而有其专门的针对性,与诸如兼爱说基本无涉。 二、时代背景 考察一个人的思想,需先考察其所立论之时代背景;特别是,当一位思想者所提出的观点,乃是针对其时代弊端而有所感触、有所回应时,这样的考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其思想,是基础性的。 杨朱当在孟轲之前,而在孔子之后。 (一)五霸的时代 自周道衰微,春秋五霸相继而起。至少在齐桓公时,华夏大地的政治与社会风貌,已然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便如此,五霸毕竟仍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维护着华夏大地的安宁与秩序,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与生产,使人民尚且得以安居乐业。 这也就是夫子在《礼记-礼运》中所说的“今大道既隐”、“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的“小康”时代。 (二)孔子的时代 孔子的一生,处在五霸时代的末期,也就是“小康”时代的末期。是原本周代的秩序由逐步衰微与勉力维系,步入彻底的崩溃和混乱的时代。 即便如此,夫子毕竟仍生在春秋时代,列國相征,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留着经由周代伟大政治所赋予的礼信与节制;诚如顾炎武《日知录》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國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期犹尊周王,而七國绝不言王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孔子先逝,而得以无睹战國之阴诡凶残;设想夫子得见战國时代、华夏内部的极端酷烈的暴力与争夺、战乱与杀戮,该是怎样的惊诧与痛心! 然而以夫子之睿智,在经历了这个“礼乐崩坏”、“在埶者去”的时代之后,“众以为殃”将成必然,也是早已明了的了。 (三)战國时代 战國,一个大混乱与大动荡的时代。如孟轲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自是“小康”亦不存矣。 当其时,华夏大地上的人们,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被卷入到极端酷烈的争夺与战乱之中;尽管作为大争之世,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利、爵禄、利益的激励,但是,这种种激励,却往往是建立在“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样的相互残害的现实之上的。 (四)杨朱所在的时代 孔子晚年自承:“吾道穷矣”,而战國诸子们却如《庄子-天下篇》所言“各执一以为是”,虽然其提出的种种设想与方法并不真正有效,然而却更加言之凿凿。 我们无需责备他们较之夫子远为无知且狂妄;毕竟,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列國互相征伐残杀、世人追名逐利而人心不古的时代,已然没有了夫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那样的“闲情逸致”;惨烈的现实,逼迫着他们非要提出应对现实的方案并自我坚持不可。 杨朱的学说,也是这种应对的一部分。 三、杨朱学说的本意 (一)《吕氏春秋》中的阐述 对杨朱学说有非常恰当的表述的,当属《吕氏春秋》。 在《孟春纪·重己》中,给出这样的论述,“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言下之意,自我的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是失而不可复得的。相比之下,就算是天子的爵位、富甲天下,也是有可能失而复得的——尽管这种“论证”,基本是建立在妄想的基础之上的。 (二)所谓“重己”与“贵己” 《吕氏春秋》又言“杨生贵己”。那么,所谓的“重己”与“贵己”,所指者何? 不过就是重视、珍贵自己的生命——及生命之所依托的人的躯体罢了。 “重己”与“贵己”,其实也就是“重生”与“贵生”。 “生”,既可理解为生存,也可理解为生命(及所寄托的躯体)。 (三)为什么要提出重生、贵生 那么,杨朱为什么要提出重视生命、生存,劝告世人,以珍重自己的生存所依托的躯体为第一要务呢? 照理说,世人都热爱与珍惜生存,而恐惧与排斥死亡,这样的劝告,难道不是多此一举么? (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对于上面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乍看起来,人类最惧怕的,无过于死亡,所以有“贪生怕死”之说;以至于有这样的浅薄见解,即:死亡是唯一或者最大的哲学课题。 然而,在现实中,人类的行为,实际上有有意或无意的、主动或被动的,体现着对生存的轻视、对死亡的淡漠。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成语,就很好了描述了人类的这种行为特征。 “鸟为食亡”,鸟儿为了食物而可以被诱捕,仍然是基于生存的需要;但是,“人为财死”就不同了。 我们不得不问,若果人不是觉得“财”的价值高于“生”,怎么会做出“人为财死”这样的行为呢? 况且,人不止为财而死,还可以为名利、爵禄、美色、妄想甚至虚荣而死,促使人轻视生存的因素何其多! 正因此,在庄周后学写作的《道德经》里,有这样的感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五)杨朱学说的提出 正是基于类似以上的分析,才促使杨朱提出他的重生与贵生学说的。 在杨朱看来,人们为了功名利禄、财货美色而可以那样轻视自己的生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们认为前者的价值,远远高于后者么? 也就是说,在价值排序上: (财富、爵禄……) >> 生命 是的,杨朱所在的战國时代,恰恰就是这样的大争之世,是一个人们主动或被迫的轻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着彼此之间酷烈争夺的时代。 因此,对杨朱而言,解决此一问题的方法,首先就要在观念上,纠正世人的价值排序。设想,如果在价值排序上,人们能够反过来,认识到: 生命 >> (财富、爵禄……) 那么,上面的种种残酷的悲剧性现实,不就可以被避免了么。 这就是杨朱思想的本意。 是的,杨朱的思想,是很“消极”的;但是,这正是对他所在的那个太过“积极”的战乱时代,试图做出的矫正。 综上,杨朱的学说,就其核心要义而言,是非常简单的;可想而知,这样简洁的思想,纵然流行一时,也是难以单独作为一个深刻的理论而发挥长久的影响的。另一方面,此一思想,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显得过于粗糙浅薄;其有价值的部分,很容易被其它学说接纳(或者是其它学说本也具有的),而浅薄之处,也容易被驳斥和解构;终至于消融了。 在后文中,将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 四、诸子对杨朱讨论 (一)孟轲反对的理路 对杨朱学说的驳斥,最著名而又产生了最大误解的,莫过与孟轲了。 《孟子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记载,“……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又《孟子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记载,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由于孟轲把杨朱和墨子并列作为驳斥的对象,而墨子又是主张兼爱的;因此,就使得之后许许多多的人,不仔细考察思想者提出其思想所依托的时代背景,不认真研究思想者所以提出其某个观点的前因后果,不顾常情常理、肆意扭曲;或胡乱曲解思想者本人的观点以涂饰私意,或引为指桑骂槐之伎俩。特别是近百年来几代愚昧文人,种种无知无耻,不胜繁举。 而当明了上面所述杨朱的基本观点,诸位读者就会明白,孟轲的杨朱的反驳,正是建立在对杨朱思想的准确认识之上的——并且,这一准确认识,丝毫没有诸如贬斥杨朱为自私自利之徒的意谓。 杨朱说,现实中,“人为财死”的现象屡见不鲜,基于这种价值排序,人世间的残酷竞争和伤害将不断延续。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让人们对生存(及其说依托其躯体)的价值的重视,远远超过导致人类弱肉强食的种种诱惑的价值。 孟轲正是顺着杨朱的推理方式,用进一步推论的方式来指出其理路的缺陷的。 孟轲认为,是的,如果在价值排序上: 生存 >> (使人不顾死亡而激烈争夺的种种诱惑) 那么,理论上,确实是可以让人们由此而拒斥这些使人类陷入惨烈争夺的种种诱惑的。并且,视前者的价值越高,与后者相差越大,自然效果就会越好;以至于,能够珍惜自己的躯体,达到“拔一毛”都不愿意的程度: 生存 >> (使人不顾死亡而激烈争夺的种种诱惑) 那么,这里推理方式,或者说理论上的矫正方式,其效果自然是最好的了。 但是,问题来了,假使一个人如此珍惜自己的躯体,把生存的价值看的这样高,就难免于出现这样的尴尬:其在远远超过对世人有害的价值的同时,也会远远超过对世人有益的价值。 因此,基于这样的观念,纵然理论上可能避免人们作恶,却也同时使得人们无法为善了。 这才是孟轲反驳的要点。 (二)韩非对杨朱批评 《韩非子》言:“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世也。……今上尊贵轻物贵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可见其所述杨朱之徒乃“轻物贵生之士”,其对杨朱思想的理解与阐述,与《吕氏春秋》和孟轲的理解相同;至于其站在注重功利的立场上加以批判,也是非常自然的。 韩非的批评,同样非常恰当的表明了杨朱观点的意图;恰好在相反的方向上,证明了那些认为杨朱持有的乃是自私自利观点的人的浅薄与荒谬。 五、汉代对杨朱思想的解读 (一)《淮南子》中的杨朱思想 《淮南子》作为汉代著作,仅能凭借诸如上述的少量文献资料来理解杨朱。其记载杨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是一种基于道家所谓“返璞归真”立场对杨朱思想的理解,纵然不说是一种误解,也是对杨朱的带有非常大偏向性的解读;仅一句“不以物累形(体)”勉强可说近于杨朱思想。 (二)《列子》中的杨朱思想 在世传的关于杨朱事迹与思想的文献,除了《列子-杨朱第七》外,其它著作中只是寥寥数语。 然而考察《列子-杨朱第七》中大量关于杨朱及所谓“与其思想相关”的各种人物与故事的虚构,其中心思想,乃是一种衰败时代的权贵的纨绔子弟所特有的颓废、萎靡、放荡与做作的浅薄而又虚伪的诡辩之辞,经不起多少现实与逻辑的反驳;更和杨朱的思想本意没有什么关系;于此不作赘述。 可见,即便到汉代,人们对杨朱的思想的理解,也陷入不知所谓的境地了;而此后,这样的肤浅认识,一直都没有被修正;到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输入,诸如胡适学识极为浅薄之流,各种谬见更是甚嚣尘上,无足赘述。 六、对杨朱学说的讨论 (一)杨朱思想中的合理部分 杨朱提单出的“重己”观点,乃是基于价值对比的的躯体至上主义,简洁明快,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鲁叔孙昭说:“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到可作为杨朱思想的先启,意义则更为广泛深刻。而《孝经》中“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表述,也含有意义相似的成分。 (二)杨朱逻辑中的不足部分 为了矫正过度“积极”的现实,杨朱的思想是“消极”的;然而这样的消极,作为应对过度“积极”的现实的方案,又是远远不够的。 杨朱的这种思考,毕竟仍显肤浅。不说上述的孟轲的理论上的驳斥;以其单向度比较方法,想要应对高度复杂世界中酷烈争夺的弊端,也是有心无力的。 世间固然不乏“人为财死”的现象,但是,如同“鸟为食亡”这样的窘迫之事,也绝非不可想像的——特别是在杨朱所处的时代。于是在庄周后学的一本类似读书笔记的书——《道德经》中,干脆就给出这样的表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以十分之三的“死之徒”,与十分之三的“动之于死地”,总共十分之六的比例,来概括惨烈的现实。在此书中,还有不烧就杨朱思想的笔记、推演和滥用。 在更早的、同样掺杂了不少杨朱思想的《庄子》一书中,诸如《养生主》言;“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又或《庄子-人间世》言:“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然而,这类论述,终究也不过是无力面对现实,而故作空泛之谈罢了;在某些情境中或可有一定的心理调节与安慰作用,但也仅此而已了。 七、总结 综上所述,杨朱学说就其根本而言非常简洁,很容易说清楚,其利弊也很显然。 杨朱的“重己(生)”,非但不是什么自私自利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之所以提出“重己(生)”,正是期望以此对世人的自私自利的互相争夺与相互残害,给予约束与纠正。 陈焕章在解释夫子为什么“罕言利”的问题时,非常深刻的指出:“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 由于是对现实的矫正,才使得杨朱的学说,能够在一段时期内,与墨子学说一起,在酷烈的战國时代“盈天下”;而由于其学说的粗简,也难以流传于后世了。 八、附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者思想的方式 研究一个对现实问题有所反映或者回应的学者的思想,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其所面对的现实。然后提问:这位学者是对他认为的美好的现实的解释和分享呢;或是对其实不那么美好的现实的涂脂抹粉或别有图谋呢;抑或是对不幸的现实试图做出某种矫正呢;甚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试图尽可能如实的陈述现实呢? 基于不同的状况,其所预先认知的“现实”,与其所在时代的具体现实,是否真的高度契合呢?纵然其所认知的现实是非常可靠的,其所提出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或者,其提出某种说法,含有怎样的图谋呢?其对不幸的现实试图做出的矫正方案,是否真的具有、或者具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特别是,由于古代中国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内部认同度较高的、具有庞大人口数量的人群,使之无法如同小规模人群那样,通过对外的掠夺和转嫁来有效缓解内部矛盾;反而常常要对面人口数量非常少的他方人群的掠夺压力。古代思想家们,都要面对这个基本事实,因而他们对现实的研究与应对,难免于致力于对内部弊端有所矫正和改善的尝试;因此当看到他们的某个思想,就必须首先提问:这是想要应对怎样的、甚至与其观点截然相反的事实呢?那样的对现实的认知是正确的么? 比如说,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已对当时甚至更早时期的现实,写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论断;即便如此,司马迁恐怕也很难设想,到了宋代,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到,如伊沛霞在《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所深刻论述的:“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通过谈判、买卖解决的世界”;而当时儒家学者“想把人们固定在限定好的角色位置上”,正是试图对这个高度势利和市侩性的现实,面对一个高度个体意淫化因而高度涣散的人群,试图做出某种矫正。 至于这些思想的现实有效性如何,这是到研究的较后阶段才要讨论的问题。(尽管,由于在前工业时代,以华夏的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当时对大自然的低下的有序获取能力,他们的方法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徒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