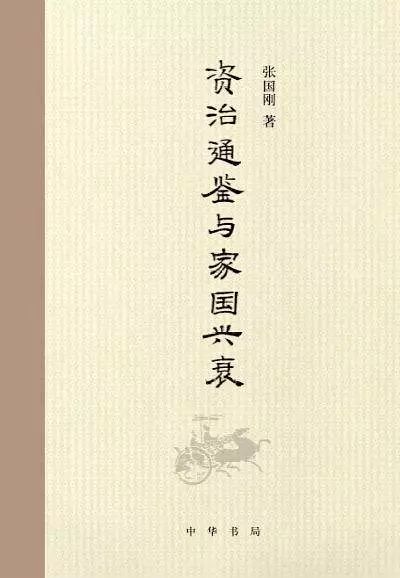汉武帝 东汉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汉武帝当朝大臣汲黯却当面批评自己的“老板”:“内多欲而外饰仁义”!搞得汉武帝十分尴尬,“默然良久”。退朝后对身边的近臣说,汲黯这家伙太粗暴了! 今日对于汉武帝的评价何尝不是如此!本文就集中谈谈所谓“独尊儒术”问题。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通鉴卷17)董仲舒对策是否如《通鉴》所载,系于武帝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年),胡三省依据司马光本人的《考异》已经表达了异议。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学术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第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尊崇儒术究竟是在即位初年,还是大约十年之后,公孙弘第二次对策之时?第二,汉武帝是否真的如《汉书•武帝纪》“赞”总结的那样,“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还是尊儒的同时,依然“悉延百端之学”?(史记·龟策列传) 第一个问题涉及提出政策的确切时间,属于技术性问题,可以不具论(综合现有资料看,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当在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前后)。第二个问题涉及汉武帝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政策问题,不能不论。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最早记载了汉武帝政策转向之事:“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汉武帝及其朝臣提倡儒学,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符合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也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是可以肯定的。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经和儒学地位的政策。比如,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员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经明行修”(熟悉六经,修养品行),射策选士,成为士人进身官场获得利禄的最重要途径。官府的引导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读书人,“靡然乡风矣”。 但是,正如班固所说的,就汉武帝用人实践来说,绝对是不拘一格的: “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燕爵,即燕雀。“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此句谓,三人在位汉武帝启用之前,都怀有大才,就像是被燕雀讥笑的鸿鹄,未能展翅。),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卷58) 在一连串的名单中,能够称得上儒学出身的,似乎只有公孙弘、董仲舒和倪宽。但是,在汉武帝器重的这一串名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功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心思比较灵活,具有实际政务操作能力,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以(倪)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汉书卷58)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元封五年,汉武帝以朝廷缺乏文武人才,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通鉴卷21) 
董仲舒 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方面批准丞相关于“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通鉴卷11)的奏章,因为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或者说印证了汲黯的观察,即汉武帝志在高远(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礼教。 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唐太宗说过:“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帝范》)道与术的问题,也是儒家常常讲的“经”与“权”的问题。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所谓“以正治国”——经,“以奇用兵”——权。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 “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到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此“独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学”),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社会失序问题,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影响深远。儒学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儒学成为一种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于是,腐儒、陋儒、伪儒、神儒(谶纬化了的儒学)也纷纷出现。汉元帝为太子时主张“纯用儒生”,已经令汉宣帝忧心忡忡:乱汉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决利中有弊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时”与“势”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化,对于治国之道、化民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兼济、礼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审“时”度“势”,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懂世异,不知时移,就会胶柱鼓瑟,适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十分可笑了。 (来源:公众号“凤凰国学”2017-09-13) 【张国刚读史专栏 · 品读《资治通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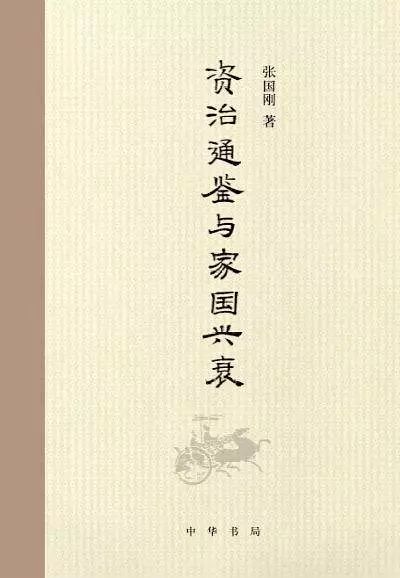
|



_22263948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