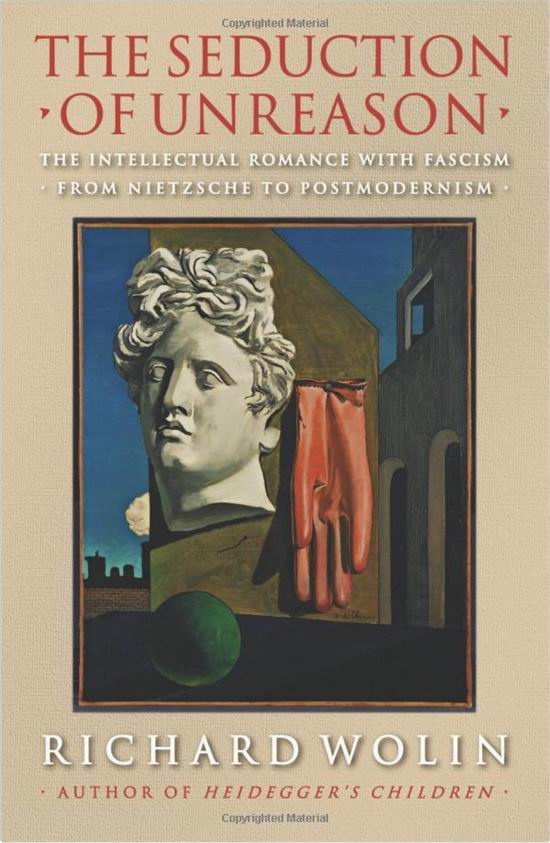《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原文原版
【内容提要】
本文以理查德·沃林新书《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以及以赛亚·伯林的相关著述为依据,对反启蒙思潮与极权主义的关系展开思考。文章首先借助伯林的著作,概括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重点清理了反启蒙思潮——包括传统右派和后现代左派——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文章指出:应该超越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探讨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在反启蒙上共享的诸多立场。文章尤其重点分析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极端反本质主义知识论最终走向了对真理和理性的敌视并导致其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甚至并堕落为极权主义的帮凶。关于如何才能既继承启蒙思想又超越启蒙思想,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多元普遍主义的理论假设。
理查德·沃林的新书《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从一个独特的观察开始:“有些人一厢情愿地认定,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智现象(它的确有反智的一面,引者按),只能吸引罪犯和恶棍,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然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当年欧洲大陆有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争先恐后地跳上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列车。” 20世纪80年代被曝光的大量档案资料表明:二战时期德国学术界与纳粹的勾结与合作(包括组织行动上的,但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以至于1998年德国历史学会年会期间,与会者大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诸多前辈“当年曾致力于正当化纳粹种族灭绝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事实让人感到惊悚,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并不比别的阶层更能抵抗极权主义的诱惑,它也印证了电影《浪潮》的主题: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绝非只是大街上流浪的没文化、无知识的地痞无赖。恰恰相反,极权恐怖故事也可能发生在精英荟萃的高等学府。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法西斯主义同样有着挡不住的诱惑。电影中的大学生们仅一个星期就从温文尔雅的年轻学子变成了凶神恶煞的纳粹狂徒。
极权主义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中间存在必然联系吗?被誉为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却原来是一个极容易迷失于极权运动的群体吗?这不仅是沃林这本新书要处理的一个思想史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二战后自由主义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而痛苦的问题。
一、启蒙精神及其背叛
沃林认为,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亲极权主义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否弃启蒙运动及其确立的人类基本价值。那么,在反启蒙和亲极权之间存在必然关系么?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讨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何为“启蒙”?何为“反启蒙”?
由于“启蒙”概念的内在复杂性,本文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它进行系统详细的语义梳理。笔者想选择一个简单的方法,即采用以赛亚·伯林关于启蒙和反启蒙的基本界定和描述。之所以选择伯林,一方面因为伯林的西方观念史研究特别聚焦于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反启蒙思想家(比如维科、迈斯特、赫尔德、哈曼,以及其他浪漫主义思想家),而研究反启蒙思想家的前提则是熟悉和精研法国启蒙思想。伯林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观念史研究专家。
伯林的几乎每一本书都会涉及到对启蒙的理解问题,但集中探讨启蒙概念的则是其《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一书。此书单辟“启蒙运动”一章,对启蒙的内涵做了集中阐释。伯林指出,尽管启蒙运动内部有很多分支乃至分歧,“但是也存在着对整个文明和进步的某些或多或少共同的信仰”。 这些信仰包括:第一,“世界或自然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受到唯一一套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原则上是可以被人的聪明才智发现的”;第二,“统治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规律原则上与统治植物、动物和有知觉的存在物的那些规律是一样的”;第三,“存在某些可以公正地说所有人都在追求的客观上可以认识的人类目标,即幸福、知识、正义、自由”,“这些目标对所有人都是实际上共同的,并非不可实现的,也并非不相容的,人的痛苦、罪恶和愚蠢主要是由于对包含着目标的东西的无知,或是对实现它们的手段的无知--而无知反过来是由于对自然规律认识不充分。” 他紧接着又把上述对启蒙精神的描述概括为启蒙所依赖的“三个最有力的支柱”:“对理性的信仰,即依赖证明和确证的逻辑上相互联系的规律和概括结构;对超越时间的人的本质的同一性和普遍人类目标的可能性的信仰;最后,相信通过实现第一个支柱,便可以达到第二个支柱,相信通过受到逻辑和经验指导的批判智识(它原则上能够把万物分析至最根本要素,能够发现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遵循的单一体系,由此,但凡是清楚的头脑为了发现真理而提出的一切问题,它都能够解答)的力量,可以确保物质和精神的和谐和进步。” 而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启蒙精神被伯林更加简要地概括为“三个中心原则”--普遍性、客观性、合理性。 应该说这是对启蒙精神非常精要的概括。
相应地,反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张扬与这三个原则正好相反的另外三个原则,即,特殊性原则(比如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主张具体事物和价值的相对性和差异性),主观性原则(比如浪漫主义对自由意志的崇尚)和非理性原则(强调情感、直觉及体现它们的诗歌和文学的价值)。
理查德·沃林显然继承了伯林的启蒙观。在《法西斯的魅惑》的“导论”中,他这样概括启蒙精神:1、启蒙主义者自命为“人性党”,“代表人类公意,而非特定利益集团”;2、高举理性旗帜,“分析并消解各种教条、迷信和缺乏正当性的社会权威”;3、政治上主张民主共和。当然,具体到某个人,情况又是比较复杂的,有些人可能兼有启蒙和反启蒙的思想,而有些人则很难被截然划分为启蒙者或反启蒙者。比如卢梭。一方面,从其推崇直觉和情感的角度看,他可以被纳入反启蒙行列;但作为《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显然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法国大革命的理论领袖,普遍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试图把极权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启蒙理性的异化,但沃林(一定意义上也包括伯林),都把反启蒙视作极权主义的根源(当然,相比于沃林,伯林对启蒙有比较多的反思,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赫尔德等多元论者的推崇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积极自由的警惕上。他的思想更有张力)。伯林明确把18世纪哈曼和约瑟夫·德·迈斯特等反启蒙思想家视作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伯林认为迈斯特及其追随者秉持的是“反启蒙运动的最黑暗形式之一,也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的形式之一”,他们“构成了十九世纪初欧洲反革命的急先锋”。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迈斯特等人的)这些沉闷的学说,在法国变成了鼓吹君主制政治的灵感之源,并且和浪漫的英雄主义观念,以及在创造性与无创造性、历史和非历史的个人及民族之间所做的明确划分一起,大大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后则是它最野蛮最病态的形式--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学说。” 伯林的另一篇文章《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专门分析了迈斯特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这个一向被认为古怪、老朽、暴躁、冷酷无情的宗教皇权和世俗王权的捍卫者,在伯林看来却是一个“非常时新”“具有先见之明”“超前于时代”的人物,他在当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的学说、甚至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趋向,不得不等待一百年之后才能自我实现”。 这个所谓“自我实现”显然就是指百年后发生的法西斯运动。伯林在迈斯特所赞赏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恐怖景象中,发现了其与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偏执世界观的“亲缘关系。” 迈斯特认为,支配整个动物界、植物界和人类世界的是弱肉强食的暴力逻辑,“有一种力量,一种暴力,亦隐亦显,在每一种物种里面,选定一定数量的动物要去吞噬另一些……无时无刻,都有某种生物正在被另一种生物吞噬”。 而人类,作为所有动物中最高的物种,“杀戮以求食;杀戮以取衣;杀戮以为打扮;杀戮以为攻击,杀戮以求自保;为了锻炼自己而杀戮,为了愉悦自己也去杀戮;他为了杀戮而杀戮。他是洋洋得意的恐怖之王,想要得到一切,谁也不能阻挡”,“整个地球,永远浸泡在血泊中,无他,一个巨大的祭坛而已。所有的生命都必定要被献祭,没有目的,没有选择,不会停歇,直到万物的终结,直到罪恶的根除,直到死亡都死亡”。 迈斯特歌颂这个恐怖世界的最强者,即刽子手,“一切的伟大、力量、服从都依赖于刽子手”,没有了刽子手,“秩序马上就会陷于混乱:王权倾覆,社会动荡”。 这些刽子手的使命是尊奉“神意”,冷酷无情地维护秩序、消灭敌人。“造物主”已经安排了等级分明的秩序,也指定了需要消灭的敌人:新教徒、自然神论者、科学家与民主人士、自由主义者、平等主义者。这个疯狂的反革命潮流,“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而达到了顶峰”。 迈斯特的这套暴力杀戮“理论”尽管披着“科学”的伪装,实际却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预言,在其中分明可以听到希特勒的大灭绝之声。
伯林对迈斯特与极权主义关系的分析深得沃林的赞同。《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写道:“伯林的确言之有理,因为法西斯主义宣誓的目标之一,就是要终结19世纪源自启蒙的世界观:崇尚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法西斯的魅惑》,第3页)沃林对从尼采到后现代的反启蒙思潮及其与极权主义关系的清理,基本是在上述对启蒙和反启蒙的理解基础上展开的。他的论旨集中概括一下就是:在反启蒙的共同目标和纽带下,左和右、激进和保守各种思潮都会在亲极权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二、超越左与右
一般认为,极权主义可分左右两翼,其代表分别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它们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反思极权主义的学者既有自由主义者或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他们反思的对象主要是苏联模式的左翼极权主义;也有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思的对象主要是纳粹的右翼极权主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很难归入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反思的对象既包括法西斯主义也包括斯大林主义。不同阵营的学者在探究极权主义的源起时,找到的原因常常不甚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其中最戏剧性的是:现代性,尤其是现代启蒙主义,在有些学者那里被视作造成极权主义的元凶(比如霍克海默、鲍曼),而在另一些学者--比如沃林--那里,极权主义的产生恰恰是因为背叛了启蒙主义,因而,反启蒙思潮和极权主义的关系也就成为很多学者集中讨论的主题。
沃林的《法西斯的魅惑》的基本结构是:除了“导论”和“结论”采取总论形式外,第一部分“重探德国意识形态”聚焦于德国知识界三位右翼思想家,即尼采、荣格、伽达默尔,同时广泛联系到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密特等其他当代德国右翼思想家,以及18、19世纪的德国反启蒙思想家,如维科、赫尔德、迈斯特、费希特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启蒙,其中不少有非常明显的亲纳粹言行。第二部分“法国的教训”转向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巴塔耶、布朗肖和德里达,连带也涉及到福柯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同样是反启蒙,其中有些同样有明显的亲极权主义倾向。除了这两部分之外,本书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安排了两个“政治附录”:第一部分之后的“德国新右派”和第二部分之后的“法国新右派”。所谈均为法西斯主义在当代德国和法国政坛的最新案例,表明“反启蒙思想并非明日黄花”,它在当代欧洲还大有市场。
该书反复出现的“右翼/派”“左翼/派”“新右翼/派”“新左翼/派”有时不免令人眼花缭乱,但有一个重要主题始终贯穿其中,即极权主义不分左右。作者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第三帝国时期“争先恐后地跳上法西斯战车”的知识分子精英,既有德国右翼(俗称“保守主义者”),也有法国后现代左翼(俗称“激进主义者”)。前者(如尼采、海德格尔)因其与纳粹的明显关系(尼采哲学被纳粹奉为御用哲学,海德格尔则一度成为纳粹哲学的代言人并加入纳粹组织)在德国曾经名声狼藉。但有意思的是:二战后这些右翼思想家却摇身一变而为法国知识界后现代左派(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的偶像。用沃林自己的话说:“当代的怪相之一,就是对启蒙运动的传统发动攻击的人士,除了向来质疑它的政坛右派之外,还有一批摩拳擦掌的学院左派”,“反启蒙思想的论述原本是政坛右派独享的专利,如今却在文化左派的代言人手中重获新生”。 这是一个吊诡,因为对于理性和民主的怀疑和讥讽,原本是“反动思想”(保守派或右翼)的注册商标,“如今却已然成为后现代左派的一贯立场。”
这样,清理反启蒙思潮--包括传统右派和后现代左派--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而不是纠缠于左、右之别,成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习惯了左右二元对立思维的读者会对此大感迷惑:在宏观社会理想与具体政治立场上差异巨大的左翼和右翼,怎么会都成为极权主义的拥护者?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曾经有过分析。此书通过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的语境中,“左”“右”概念常常含混不清 ,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虽然是极权主义的两种类型,但本质上它们是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义“混同政党和国家,控制独立的组织,把有偏见的学说转变成一种全民族的正统学说,诉诸暴力并赋予警察无限的权力”。 而这些难道不也是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主义的特征吗?有人会反驳说:法西斯主义源自反革命的浪漫主义 ,而斯大林主义则来自革命的理性主义。或者说,前者强调特殊性,而后者标举普遍性。对此,阿隆这样回应:“号称左翼的极权主义在革命发生三十五年之后,却颂扬大俄罗斯民族,谴责世界主义,维持治安和正统观念方面的严格规定。换言之,它继续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是启蒙运动在反对权力的专断和教会蒙昧主义的过程中力图倡导的。” 正因为这样,阿隆说“法西斯伪右派”(希特勒政权)和“苏联伪左派”(斯大林政权)“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
与阿隆相比,沃林通过很多新的实例和材料,进一步深化了“左”“右”两翼在极权主义这个交叉点上混合难分的主题,从而极大地强化了该主题的当下性。比如,德国“新右派”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势下出现的,它的策略也随这一情势进行了调整:1、一方面,以“民主右派”自居,以区别于“纳粹右派”或传统右派,扮演温和角色,适度左转。另一方面,在吸收一些左派思想家(比如葛兰西)的观点时又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其作右倾化阐释,以撇清自己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可谓左右逢源。 2、把对抗“西方价值”和启蒙,与对抗“左”派极权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甚至把1968年革命等同于纳粹。3、选择性地解释历史,包括选择性解读纳粹主义,把德国在二战中的遭遇书写为受害者的历史和德国分裂的开始,淡化或回避德国给其他民族造成的灾难。 新右派领导人声称:“当务之急是将第三帝国的罪行相对化和尽可能淡化。”
在右派貌似向“左”转的同时,“左”派则貌似向“右”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竟然和右派一样,也是1989年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名声狼藉。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传统就是崇尚民族和国家,否定这个传统,左派在德国很难立足。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出现了如此现象:“从1989年开始,‘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极权本质原形毕露,左派知识分子从此失去了可资追求的乌托邦,对许多人而言,‘国家’的概念似乎成为达到相似目的的最佳选择。”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就是所谓“民族布尔什维克”
左派和右派于是乎同仇敌忾,共同质疑现代性,共同反对普遍理性、科技和市场主导的现代社会,共同向往计划体制、独裁政体、民族主义三结合的社会模式。它们也都憎恨中产阶级社会及其文化(视其为庸俗市侩),推崇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和文学,仇恨美国大众文化(因此这种憎恨是阶级仇与民族恨的混合,美英等国被视作中产阶级的代表)。亲纳粹的结构主义大师斯特劳斯的《澎湃的山羊之歌》把“电视公众文化体制”视作“暴力但不流血的最高主宰形式,也是历史上最无所不包的极权主义”。呼唤神秘经验,倡导“美学的存在体证”,高度赞美尼采的“生命是一件自我创造的艺术品”,倡导“审美国度”(aesthetic state),通过暴力的美学仪式达到“共同体的凝聚”。他们认为自德国浪漫主义以来的传统精神优势“正在淹没在群众社会的肤浅现象之中:消费主义、广告、好莱坞,以及广泛的文化产业。一言以蔽之,‘美国主义’。”
不过,尽管后现代激进左派存在沃林所说的“右倾化”现象,但把它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奇怪:不同于具有明显亲苏倾向的传统左派,后现代左派普遍放弃了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幻想。同时,在主张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差异性乃至碎片化,崇尚反本质主义,反对绝对真理方面,后现代左翼与极权主义的一元论真理观似乎难以调和,而极权主义的国家强力崇拜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似乎也相去甚远。那么,它是怎么和极权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这个转换是如何完成的?
显然,沃林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可以简单划等号,也不认为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会成为极权主义者。他明确说:“后现代主义者在政治上各有主张,然而很难一概说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尽管本书的主旨是要探讨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纠葛,其中有几位是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但是我无意于将他们连坐入罪。” 但是,两者之间的亲缘性也是明显的,因为它们分享诸多共同的观念与信仰:无论是希特勒还是迈斯特、哈曼等极端保守派,抑或20世纪上半叶的超现实主义者(其中很多同时也是法西斯分子),直至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不满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厌恶现代性的平淡无奇、单调贫乏,认为理性不是解放了人而是变成了对人的另一种压制形式。这些人都崇尚非理性的奇迹、强烈的情感刺激,必要时对暴力青睐有加。
但后现代主义与极权主义直接联系的证据可能不多。其实它的主要危害在其极端反本质主义(主张不确定性、自发性、极端差异性,反对确定性、一元论、绝对真理)最终走向了对真理的敌视、对理性的攻击,走向了真理和价值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尼采的视角主义、权力意志,到福柯的知识即权力),导致其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甚至转化为政治犬儒主义并堕落为极权主义的帮凶。 这种政治犬儒主义即使不会赤裸裸地鼓吹极权主义,也很难指望其能有效抵制极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的暴政”,张扬差异与歧义,他们排斥“共识”,将之等同于“恐怖暴力”,认为所谓非强制性的理性协商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如此等等。但问题在于:如果确实一切知识、真理不过是权力的运作,根本没有普遍的有效性基础,那就必然导致知识论虚无主义,并进而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和政治犬儒主义,导致行动的瘫痪:我们有何凭据在不同的观点之间选择并以之作为行动依据?“如果福柯所言为真,‘权力’无所不在,那么质疑它也变得毫无意义。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实际挑战宰制的力量,他们宁可恋栈相对而言较安全的‘元政治’领域--那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天地,主要的风险仅止于‘观念’,而实际政治则化为虚无缥缈之物。” 这的确击中了后现代主义的要害。
更有进者,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特殊性以及建基其上的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但离开了人权、平等、正义等启蒙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的框范和制约,上述知识论的诉求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上的“本真的”种族特性崇拜,拒绝民族、人种和文化的混合,最后与右翼极权主义殊途同归,走向种族隔离主义和文化分离主义。 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大量发生在阿拉伯、南美和非洲国家的事实所证明。比如在卢旺达这样的宪政民主尚未建立的地方,认同政治就引发了种族屠杀之类“难以形容的悲剧”。这进一步证明了“认同政治”作为一个反普世价值的后现代概念,其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危险性是不同的:认同政治着眼于人的非自主选择的特殊身份归属(如种族或性别),而不是普遍公民身份,因此类似于一种出身论。但只有在一个由宪法法制保证的政治空间和以普遍人权观念有效调节族姓身份观念的思想空间中,认同政治才能得以和平、合理展开,因为前者为后者“创造出了一个政治空间,一道免于政府干涉的‘魔墙’,可以说,人们在此可以各种方式安全无虞地探讨文化认同各项要素,而不至于鄙夷践踏其他与之竞逐的认同要素。” 因此,“要确保相互包容与共存共荣的价值,程序民主的正式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