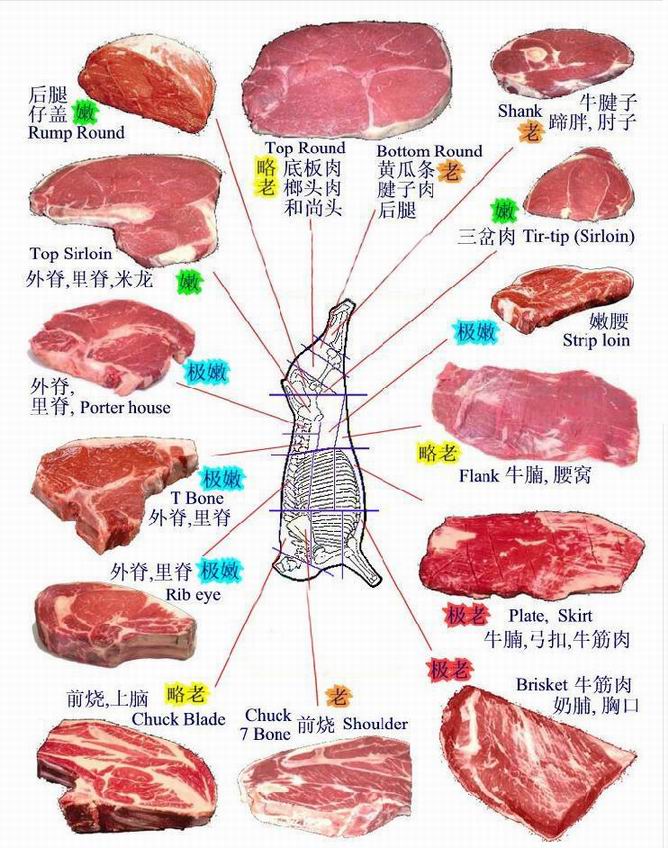摘 要: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同合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庄子》成于战国中晚期,现存三十三篇,为道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远”,司马迁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言汪洋恣肆以适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庄子》把深奥玄妙的哲理与生动具体的工程技术熔于一炉,其想象丰富,内涵深刻,不仅使抽象的逻辑思维与具体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而且使我们一窥先秦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探讨《庄子》中的技术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科技人员的创新与素质教育颇具现实意义。
1 道艺合一
是重道轻艺,还是道艺并重,历来是各家对待“道”和“艺”这对矛盾态度的分水岭。《庄子》主张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道艺合一,是庄子技术思想的灵魂。
《庄子·天地》篇提出:“故通于天下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道,德兼于道,道兼于天。”事,即百宫之事,“能有所艺者,技也。”艺,即树艺,犹今天所说的生产技术,易能而曰技,为其有所专,“技兼于事”的兼,统也,技各有所专,此为其所长,而专则不能相通。郭象注:“夫本末之相兼,犹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则百节皆适,天道顺则本末俱畅。”这段的中心思想就是道艺合一。《庄子》“技进乎道”的思想使“道”“艺”进入合一的境界。
《庄子·天下》篇提出“道术”一词,该篇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述者,恶乎在?曰:无乎不在。”也即言“道”与“艺”而为一。《庄子·在宥》篇云:“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圣耶?是相于艺也。”礼言“相于技”者,五射五御,皆有其礼,不独周旋,揖让而已,故礼近于技。相者,助也,即助长之谓。“说”音义同“悦”,圣言“相于艺”者,《尚书·金腾》篇中有:周公“多才多艺”,《论语·子罕》篇中有:孔子“多能鄙事”,艺固圣者之事也。“礼”“圣”都是“道”,“技” “艺”都是“艺”,前者有助于“相于”后者,就成了道艺合一。这个道理与《老子》相同。
《庄子》的新贡献在于用形象构成故事。形象给人总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形象就是一个整体,读者从中体悟这个道理,体悟的道理才是完整的。言说的道理总是挂一漏万,因为从概念出发总是片面的,《庄子》以庖丁解牛、梓庆削大马捶钩、轮扁斫轮诸事,阐述道艺合一的思想。
(1)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见《庄子·养生主》。庖丁,谓掌厨丁役之人,亦言丁名。《庄子·在宥》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此言解牛者,盖以牛为大物。许慎《说文》“物”云:“万物也,牛为大物,故从牛。”故以宰国寓之于宰牛,而终归养生,所谓养生为主。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像一场神妙的音乐舞蹈:奏刀若奏乐,所以有“合于桑林之舞”、“中经首之会”之文。“桑林”乃汤之舞,“经首”乃尧之乐。庖丁解牛与“桑林”的步伐和“经首”的节拍相吻合,声有粗细,而参错中节,故曰:“莫不中音”。文惠君曰:“讠喜,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解刀对曰:“臣之所以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的答话十分重要,其意谓道于是乎在,不得以技视之。道进乎技,则道艺合一。《天地》篇云:“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兼犹包也,自上言之则曰兼,自下言之则曰进。进犹过也,过乎技者,技通乎道,则非技之所得而限。庖丁所言“所见无非牛”,“盖诚用以于一艺,即凡天下之事,目所接触,无不若为吾艺而设。必如是能会万物之一己,而后其技艺乃能擅天下之奇,而莫之能及。技之所谓进乎道者,在此。”而其“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由有此工夫而致。《庄子》强调“未尝见全牛”,分肌擘理,表里洞然,如指诸掌,所谓“及其久也,相说以解”,故无全牛。“神遇而不以目视”,说明目之用局而迟,神之用周而速。“官知止而神欲行”说明非止不能稳且准,非行不能敏且活也。“依乎天理”,即“照之于天”,“依自然之涯分”,因其固然,即顺物自然。“技经肯綮之未尝”,郭象注:“技之妙也,常游刃于空,未尝经概于微石且。”“依乎天理”是庖丁解牛的经验。这里的“天理”就是牛的自然结构。成玄英疏:“依天然之腠理,终不横截以伤牛。亦犹养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不必贪生以夭折也。”贾谊也列举过类似庖丁解牛的例子。其《新书·制不定》载:“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刀不钝者,所排击,所割剥,皆众理解也。”理是指事物的文理结构。《韩非子·解老》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又说:“理者,成物之父也”,指的是物的外部结构。贾谊在《等齐》篇中讲的“天理则同”,也说的是人的面貌等生理结构是类似的。这表明,理是表示事物结构的概念。
庖丁回答文惠君的“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对“道”与“艺”关系的总结,道进乎技,则道艺合一。
(2)梓庆削鐻。
“梓庆削鐻”见《庄子·达生》篇。梓庆,“梓”是木工,“庆”是名,俞樾《诸子平议》谓《左传·襄公四年》中的匠庆即此人。梓匠虽异官,而同为木工。“鐻”,用于悬钟鼓之器,以木为之,故曰:“削木为之鐻”,后为青铜铸造,非梓人所得为之。“鐻成,见者敬犹鬼神”,是?有种种花纹,人惊其刻镂之巧。梓庆的经验是“心静则气充,故不以耗气,则必齐心静。”“齐”读如斋,斋以静心。亦言齐以静心尔已。达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以天合天”即《养生主》所谓“依乎天理,因其自然。”郭象注:“不离其自然,”成玄英疏:“机变虽加人工,本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而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郭象注:“尽因物之妙,故乃疑似鬼神所作也。”成玄英疏:“所以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于天性,顺其自然,故得如此。”梓庆的经验,也是道艺合一。
(3)大马捶钩
“大马捶钩”见《庄子·知北游》。大马,官号,即楚之司马。捶,打锻也。钩,腰带。大司马手下有工人,少而善锻钩,行年八十而捶弥巧,专性凝虑,故无豪芒之差失,拈捶钩权,知斤两之轻重,无豪芒之错。
王念孙《读书杂志·馀编上》“臣有守也”条云:《知北游》篇:“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马曰:子巧与?曰:臣有守也。’念孙案:‘守’即‘道’字也。《达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证矣。道字古读若守,故与守通。王氏自注:凡九经中用韵之文,道字皆读若守,楚辞及老庄诸子并同。”秦会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记·秦始皇本纪》道作首,首与守同立。《说文》道:所行道也,从首。段注:首者,行所达也,首亦声。“用之者”承“非钩无察”而言。“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承“于物无视”而言。“用之者”,技也,“不用者”,道也。此与庖丁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辞异而义同。“而况乎无用者乎,物孰不资焉”,“无不用”,不用而无不用,犹言无为而无不为。捶钩老人的经验,也是道艺合一。
(4)轮扁斫轮
“轮扁斫轮”见《庄子·天道》。此段文字,实从“世人所贵道者,书也”一句开始。以其泥于书以求道,不重视实践活动,故有古人糟粕之语,并不是说书果可不读。轮扁所言:“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即如《养生主》篇庖丁所言“官知止而神欲行”,只有实践,才能达到“依于天理”,“因其固然”的境地。轮扁可谓深得斫轮之道,实现了道艺合一。轮扁这段话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道艺合一。他体悟到,道“不可信”,“口不能”,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只能个人“得之于心,而应于手”,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语言文字虽道之所寓,但语言文字非道也。轮扁告诫齐桓公,读书要区别文字和精神。若得精神,就如《老子·第十四章》所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若不得精神,文字便是糟粕。郭象注此,亦云:“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信,与时变化,而后至焉。”也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只有亲自实践、体悟,“得心应手”才能“与时变化”。成玄英疏此,亦云:“夫圣人制法利物随时,时即不停,法亦随变。”亦寓此意。
2 道通为一
庄子提出了“道通为一”的思想,这就是《齐物论》中的“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忄危忄怪,道通为一。”这里庄子仍然强调万物自己如此,道即自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一句,如郭象所注的那样,是“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成玄英疏:“物性执滞,触境皆迷,必固为有然也,固谓有可,岂知可则不可,然则不然也。”“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忄危忄怪,道通为一,”也如郭象所言:“夫莛横而楹纵,厉丑而西施好,所谓齐者,岂必形状同规矩哉。故举纵横好丑,恢忄危忄怪,各然其所然,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道通为一也。”为了解释“道通为一”,成玄英疏:《庄子》略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忄危忄怪八事相比较,他认为,以道观之,本来无二,是以妍之状万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为一”。“道通为一”还要说明的是“通”,“通”什么。大千世界,纷纭万象,《庄子》所提出的“道通为一”,要在通宇宙,通天,通地,通人,即天、地、人,都要无所不通。惟有如此,才如《天地》篇所云:“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而要达到“道通为一”的目标,庄子认为必经分解同合之途。
(1)以道观分
《庄子》提出了“分”的思想方法。《齐物论》云:“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如《老子》所云:“朴散以为器”,郭象注此云:“夫物或此以为散,而彼以为成。”“其成也,毁也。”所谓“为”者,败之之谓,如郭象云,“我之所谓成,而彼或谓之毁。”成玄英疏:“或于此为成,于彼为毁,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则散毛成毛,伐木为舍等也。”然无成因无毁,无毁亦无成,故又云:“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言“凡物”者,以一物论,则有成毁,总物之全而观之,成亦在其中,毁亦在其中,则何成何毁。所以,郭象认为:“夫成毁者,生于自见而不见彼也。”故“我成与毁”犹无是与非。成玄英疏此也认为:夫成毁是非,生于偏滞。即成毁不定,是非无主,故无成毁,通而一之。
在《庚桑楚》中,庄子再次论述了“分”与“成”之间的关系。其云:“道通,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强调分的作用,分就是一种进步。郭象注:成毁无常,分而道皆通。分而后成物,故曰:“其分也,成也,”物成则有毁,故曰:“其成也,毁也。”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个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大道通达于万物,一种事物分离了,新的事物便形成了。新的事物的形成就意味着原有的事物的毁灭。试看,铁矿冶炼成钢铁,从矿石方面是分了毁了,从钢铁方面看是成了。而将钢铁制作成各种机械,从钢铁材料方面看是分了毁了,从机械方面看是成了。其中分与成,新与旧,成与毁都是同一个过程。这是从物的观点看物。“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郭象注:不守其分而求备焉,所以恶分也。“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郭象注:“本分不备而有以求备,所以恶备也,若其本分素备,岂恶之哉。”对于分散厌恶的原因,就在于对分散求取完备;对于完备厌恶的原因,又在于对完备进一步求取完备。若从道的观点看物,则“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因为“道能其分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的“分”、“成”、“毁”都已无意义。从物的观点看,“分”、“成”、“毁”依然客观存在;从道的观点看,“万物一府”,“万物一齐”,无成无毁,无短无长。此万物之理,此中之妙,惟“达者”知之。
《庄子》进一步指出,“自分”“自别”,《齐物论》云:“故分也者,有不分也。”即言令分则必有分所不能及。郭象注此云:“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别,而欲由己以分别者,不见彼之自别也。”成玄英疏云:“夫理无分别,而有是非,故于无分无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辨之见者,此乃一曲之士、真偏滞之人亦何能剖析于精微,分析于事物者也。”这就是《秋水》中所说的:“夫物量无究,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敌,是故大知观于远近。”
《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工艺产品设计思想的总结。今天我们见到的楚国的一些工艺产品与机械设计作品,就是庄子思想的写照,是具象化的代表之作。
楚国的工艺产品设计惯以分解、变形、抽象的手法来处理物象,以纺织品中的凤纹为例,分解的极点,或仅具一目一喙,或止得一羽一爪,变形的极点,或类如花叶草茎,或类如行云流星,或类如水波火光,抽象的极点,是化为纯粹的曲线。……这样,于形固有失,于神则有得,而且给观赏者留有广阔的想象余地。楚人的设计思想与方法表明:这种创作手法,尽管显得支离破碎,似乎非此非彼,其目的却是再现。从而分中有合,分中有继,从分解到改组和拼合也是一种创作手法,尽管显得繁杂堆砌,似乎亦此亦彼,但较之前者则是创造。分是对个体的彻底分离,犹如细胞分裂一样,只有分才有发展,但作为创作的整体而言,却分不开,分中有继,分中寓合。无疑,这一时期的中国工程技术设计乃至工艺设计达到了其他古代文明不曾达到的境界,而且达到了某些现代艺术仍在力求达到的境界。《庄子》的“道通为一”的思想,虽然并不是对于科学技术而言,但涵盖了科学技术、包括机械工程技术。
(2)不同同之
《庄子》一书不仅讲分解即“以道观分”,更讲同合,即“不同同之”。“不同同之”见《天地》篇,原文是“不同同之之谓大”。谓能同彼不同,如《周易·同人卦》所云,“能通天下之志者,是之谓大。”非曰,以不同同之。如所谓不齐之齐,郭象认为:《庄子》“不同同之之谓大”的意思是“万物万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成玄英疏:“夫刻雕众形,而性情各异,率其素分佥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谓之大。”《庄子》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然种类不同,形状万殊,但其根本之道都是同一的,这是“道通为一”思想的出发点。而“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强调万物的对立与差别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包含有某种共同点,即异中之同。又如《田子方》所云:“夫天下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意思是:世界上的科学原理是惟一的,任何设计与制造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也是惟一的。但却没有完全一样的设计和技术产品,从严格意义上说,有多少设计工作者,就有多少种设计方案和技术操作方法,就有多少种技巧、技能、经验,也就有多少千奇百怪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而其设计所遵循的规律都有一个共同基础,而其形体则可以变化。《庄子》一书所论“通于一而万事毕”,“异物同理”,正寓此意。
《齐物论》的要旨“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天地》甚至认为:“万物一府,死生同状。”万物之间无论对立、差异,都有着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德充符》所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这些思想,是我们今天创新的思想源泉。
《庄子》还提出了“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的思想。《则阳》的全文是:“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从整体上来看,世间万物,不可枚举,众必有异,然和而合之,则同者出焉,故曰:“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周易》之“同人”,说同之卦也,而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周易》之“睽”,说异之卦,而象曰:“君子以同而异”,“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所谓“合异以为同”。“系,犹悬也。”“马系于前者”,马之像悬于前也。自然界的事物,极其复杂。将纷纭繁芜、千变万化的自然事物同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不外乎自然组合和人工组合。这种组合并非简单地拼凑,而是在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的组合中,反映出设计者对事物间的相关性、对条件的适应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能力。有了“道通为一”的思想,就能“不同同之”,整合物类,不齐齐之。打通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的东西统一在一个设计的形体之中。《庄子·在宥》还强调:“大同而无己。”郭象注:“有己则不能大同也。”成玄英疏:“合二仪,同大道,则物我俱忘也。”
《庄子》“不同同之”的思想,有如今天所说的组合创造,十分恰当而巧妙地组合已有技术,同样也是创新。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思想的组合,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功能的物质产品的组合,都属异类组合。异类组合的特点是,组合对象、思想或物品来自不同的方面,一般无所谓主次关系。组合过程中,参与组合的对象从意义、原理、构造、成分、功能等任一方或多方面互相渗透,整体化趋势显著。异类组合就是异类求同,因此创造性很强。为了解决某个技术问题,或设计某种多功能产品,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技术思想或物质产品的一部分或整个部分进行适当的组合,形成新的技术,或者设计出新的产品,使之“合乎大同”。这种技术创造,叫做组合创造。
“道通为一”、“不同同之”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科学技术中进行组合创造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任何产品设计的演化与进步往往是基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想或物质的组合。要实现这种组合,任何一种技术思想和物质产品,要通过自身了解和调整后,达到新的统一,最初都需要在设计思想上开拓进展,改变对现有事物的看法,标新立异产生新的概念,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才能构筑产品的实体结构。楚国出土的大量工艺产品在设计上正是成功地利用了这种分解与组合,是科学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分中有合,合中见分,其思想之源要归于道家的“齐物论”,《庄子》阐述分解与同合的妙理,无疑是对这一时期工艺产品设计思想的系统总结。
“道通为一”是把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科学是逻辑的,是人人必须恪守的,艺术是创造的,需要想像,则兼而有之,“道通为一”是科学性与创造性有机结合的产物。从“以道观分”到“不同同之”,是启发人们透过有限渗入无限,使有限与无限相融合,避免步入后尘,因循守旧,从而使人们的创造性释放出来。
读《庄子》,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其字字句句,都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对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性,这就是《山木》篇里所指出的那样,“与时俱化”,“物物,而不物于物”,惟有与时俱进,不为外物所物,人们就能在有限的时空之中,追求无限的“天工人其代之”的目标,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创造能力。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科学技术的创新工作,特别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设计工作是一项社会性、技术性、思维性、方法性极强的创造性工作,缺乏思想的指导而仅有微观的方法是绝对不能进行创新与设计的。
本文对《庄子》所作的研究表明:《庄子》一书概括了先秦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无论是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还是《庄子》一书中对机械制造生产专业分工以及有关古代测量与加工工具的记载,都代表了《庄子》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庄子》的自然之道,尽管其本身不能直接解决科技方面的具体问题,但它的思想却向人们展现了一条探索人工巧夺天工的道路。
[1]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45.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54.
[3]涂又光.楚国哲学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4]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5]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