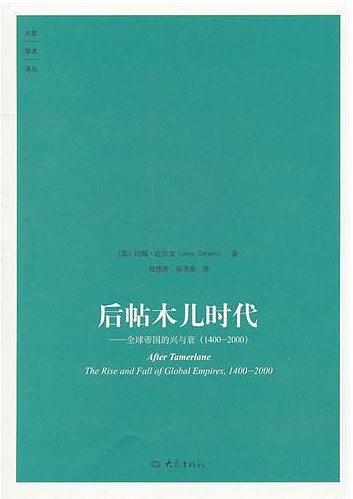20世纪下半叶以来, 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的日益频繁, 世界历史也以更加全面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随之而来的是, 运用全球史视野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一般认为, 1963 年, 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出版, 标志着全球史的诞生, 到80年代, 全球史的研究基本走向成熟。在中国, 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全球史著作, 如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泰晤士历史地图集》、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威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等。大批著作的出现, 全球史著作的中译本的增多, 表明40多年来全球史蓬勃发展的深广度。与此相关的全球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破除欧洲中心论方面有所建树。自二战以来, 虽然欧洲中心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 特别是受到学术界的诸多批评, 但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即使那些有意识抵制欧洲中心论的学者, 由于长期受欧洲中心论思想的熏陶, 在研究中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为参照, 多少会使用仅仅适用于欧洲史、只为欧洲人熟悉的术语和概念, 因此其研究结果很难说真正地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全球史家试图超越时间与空间, 站在宇宙空间, 再放眼全球, 于是古往今来的历史面貌就发生了变化。例如, 所谓欧洲的兴起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的特定时期、一个特定的阶段而已, 与人类历史上大国纵横欧亚大陆或称霸美洲大陆并无二致。按照“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并非欧洲一隅所推动,而是整个世界体系互动而成,作为互动的最终结果。牛津大学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 考察了帖木儿帝国解体后,东亚世界、伊斯兰世界、西欧世界长达600年的交锋与互动,以及其中所存在的全球化特征,有着明显反对“欧洲中心论”色彩。 达尔文明确指出欧亚大陆而非海洋是世界历史的轴心。在全球帝国中, 绝大多数集中在欧亚大陆,谁控制了这块地方, 谁就主宰了世界。因此必须把欧亚大陆的“世界岛” (麦金德的术语) 看成是世界 (以及全球) 历史的中心点及其决定性竞技场。这并不是一种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太平洋的历史学家喜欢呼应的看法, 这也有违把欧洲扩张到“外围世界”作为世界历史引擎的长期传统。但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即从世界历史长河来看, 欧亚大陆的西部、中部和东部间——也就是说, 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的关系是解释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权力和文化联系间的万能钥匙。 事实上,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 欧亚大陆的中国、伊斯兰王国、欧洲都形成了高度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 都展示了领土扩张的显著能力, 无所谓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要有的话, 也是相反。在达尔文的视野里, 地理大发现不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与达伽马或亚柏克尔克 (Albuquerque) 在印度洋的胜利、或科泰斯 (Cortes) 和皮萨罗(Pizarro) 在美洲的胜利同时发生的,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性必须对照欧亚大陆扩张主义的巨大图景来看。在他看来, 1405年帖木儿之死才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约翰·达尔文拒绝把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作为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变化的决定性时刻。直到1750年左右的现代早期阶段里, 根据其经济自主 (但不一定是他们的长期能力) 、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信来看, 欧亚大陆的所有主要文明在广泛意义上仍然是平等的。欧洲人也许沿着亚洲海岸航行和贸易, 深入到内地旅行, 刺激了亚洲的统治者和学者。 欧洲崛起的全部后果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感受到。电力和蒸汽带来的交通革命和真正的全球经济的到来, 与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帝国之间的技术资源迅速扩大的鸿沟相吻合。但是, 即使当欧洲的相对权力最大时, 也并不足以确保对亚洲的支配。在中国、奥斯曼帝国、伊朗、殖民地印度以及最重要的日本, 当欧洲的胜利几近完成时, 抵制欧洲优势的手段也得到了动员。达尔文认为, 欧洲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既被歌颂消失的殖民帝国的爱国历史学家们所夸大, 也为热心把每个现代灾难按到罪恶的帝国主义头上的后殖民主义夸夸其谈者所夸大。在达尔文看来, 欧洲经济和策略霸权也许是从1740年持续到1940年的惊人简短的篇章。然而他发现, 令人震惊的是世界政治实体的长寿和抵抗力、基于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世界 (现代土耳其) 、波斯世界(现代伊朗) 以及最重要的中国, 尽管过去的600年世事变化, 但是其边疆、语言、文化和外观保持着惊人的稳定。由此可见, 1400年以来的全球史与其说是西方崛起的经历,不如说是欧亚大陆坚忍不拔的故事。 文章来源:陆伟芳:《全球史视野中的帝国史——评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编辑原文有不少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