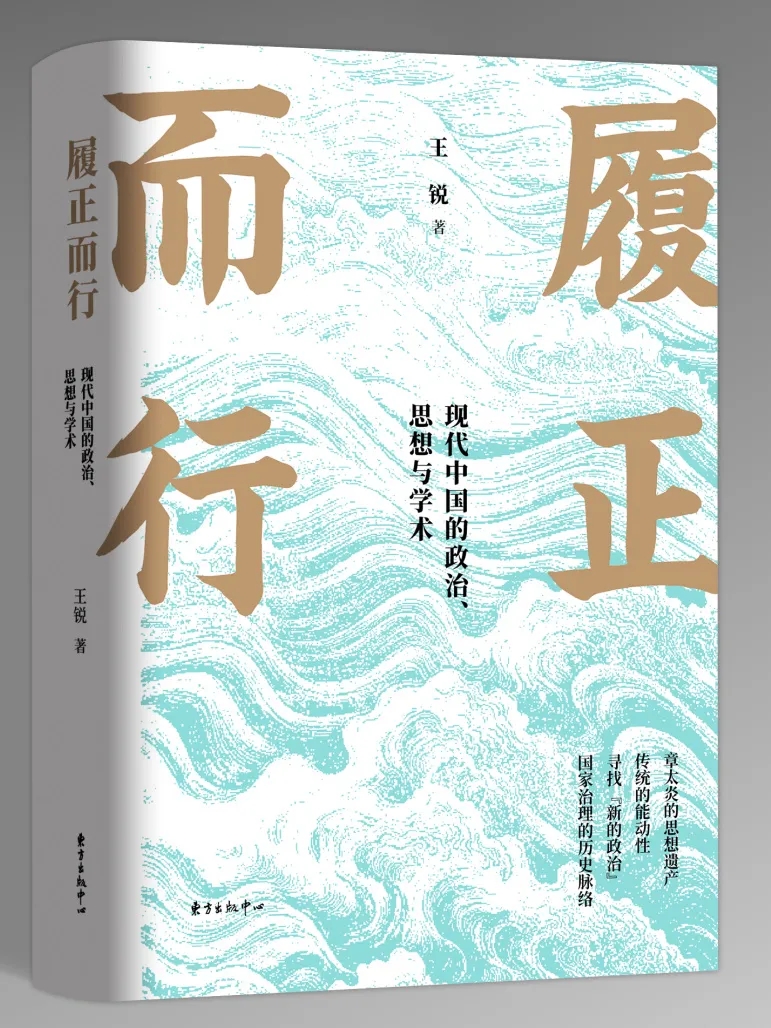秦汉以降,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以皇帝制度、郡县制度为核心的幅员辽阔的政治体,虽然在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曲折与动荡,但总体而言,这一套政治运作机制保证了维系广土众民、地域差异极大的辽阔国土;构建了具有普遍性与长久性的思想学说与社会文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彼此之间联系紧密的商贸网络。因此,分析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深入探寻。如果按照近代以来受西方中国观的影响而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简单否定,那么中华文明的核心根底将缥缈难寻,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也将大打折扣,只能沦为物质消遣层面的“小玩意”或带有极强“东方主义”色彩的博物馆之物。而要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窃以为必须充分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传统,以及根据这一政治传统而形成的古代政治。它既促进了中国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实现与巩固,并担负着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上的功能,同时在历史的流变中,也体现出一些十分明显的症结。 01“儒法传统”的几个基本特征
从《韩非子·显学篇》剖析儒家的基本特征开始,关于儒法之间的异同、儒法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表现形式就一直备受关注。总体来说,这些论争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观点:首先,认为儒家讲求道德伦理,法家强调严刑峻法,因此后者有助于巩固君权,但难以行之久远,前者具有一定“人文性”,更适合作为统治学说。而在实践当中,“儒生”也比“法吏”更有“理想主义”与精神追求。其次,自从汉武帝时期儒家被奉为官学开始,虽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容易滋生守旧、为官僚特权辩护、反对改革等弊病,因此,需要法家学说作为调剂,改革政治运作当中的各种缺失,重振政治纲常、优化政治效率。复次,把儒家学说与“士人政治”相结合,认为此乃帝制时代对抗君权的重要思想资源,反复表彰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出来的士人与君权之间的“冲突”。与之相应,则将法家贬低为“统治术”,继承了西汉以来儒生对法家的负面评价,同时把“专制”“独裁”等近代政治学里的词汇添加进来,以助声势。最后,从一种所谓“启蒙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儒法二家视为替“专制政体”服务的一丘之貉,认为二者虽然表面上各有侧重,相互间屡有冲突,但实际上在思维方式、政治主张、理想蓝图等方面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因此,都属于应被清理的历史垃圾。这一点在晚清以降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各种论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至今余音不绝。 这些观点虽然结论不同,但其实都有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并且也起到了相应的时代作用,但如果将儒法传统视为形塑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且承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对中国的发展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就需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演进脉络出发去分析儒法传统在历史流变中体现出来的特征。换言之,用古代学术话语来讲,即从“史”而非从“经”入手,用现代学术话语来讲,即避免拿基于西方历史经验总结而成的各种政治理论简单套用至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之中。 先看法家。吕思勉谓:“法家贵综覆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1]法家学说诞生于战国时期,彼时各诸侯国之间征战频繁,许多实力较弱的诸侯国被吞并,形成七雄并立局面。为了应付规模日趋扩大的战争,各国都致力于更为有效的汲取境内各种经济资源、动员组织更多的军事力量、挖掘并任用具有治国与打仗的专门人才,法家学说很大程度上既是对先前这类政治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又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分析如何更好地设官分职、建立制度、提高君权、抑制世袭贵族、管理民众、奖励军功、汲取赋税。因此,法家学说具有极强的战备色彩,有助于在竞争之世不断优化政治组织、提升行政效率、动员并整合各种政治经济资源。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法家成为了政治活动中的主要指导学说,郡县体制背后的有着极强的法家因素,比如强调主要不依靠血缘、出身,而要以客观存在的、能够经得起考核的政绩作为政治铨选的重要标准,即章太炎所谓的“问其师学,试之以其事,事就则有劳,不就则无劳”[2];还强调政治文化中应“以吏为师”,将国家的法典,以及与这些法典紧密结合的伦理规范作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由国家统筹规划,集中权力,进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打击地方豪强、杜绝世袭政治集团、收缴各地兵器这些从各个方面促进、维系大一统政权的工作。因此,通过《商君书》《韩非子》《管子》这些文献,以及考察秦政的历史流变,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法家传统的基本特征,即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国家能力的迅猛提升,巩固君权,消灭各种潜在的、有可能危及君权的政治势力,通过重视制度建设、严明法令、制定完备严谨的铨选标准,使政治组织能够有效地运作起来,保证统治集团的行政效率与客观性,同时在一定条件下扩大的政治基础,符合战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那些具备治国征战才能的人士渴望获取政治地位的诉求。而这样的制度设计、行政规范、政治文化,恰恰是有助于打破各种血缘、地域的限制,克服物质上的局限,保证一个幅员辽阔的王朝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基本的政治权威,实现政治权力对社会的覆盖。 再看儒家。儒家和周代的礼乐文明关系密切。虽然孔子修正了不少本来主要适用于周代贵族阶层之间的伦理原则,使之具有更为广阔的适用范围,并且设坛讲学,有教无类,将原本主要由贵族垄断的六艺之学普及于大众,但在政治主张和理想社会蓝图方面,孔子向往的仍旧是肇始于西周初年,以“亲亲”、“尊尊”为核心要义的礼制社会。到了战国时期,面对激烈的社会转型,孟子痛斥各诸侯国国君为了私利彼此征战,以民人填丘壑,并且提出要本于“仁心”而施“仁政”。这些观点置于当时,固然极具道德色彩与批判性,并且孟子在申说从心性修养到具体施政的过程时,从“形而上”的方面深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使之更有体系,可是孟子一方面认为战国乱局应“定于一”,另一方面却并未论述一套较有系统性的政治与社会方案,特别是缺少从制度层面与治理层面思考问题的内容,这导致其仁政理想只能在较小的共同体中实现,其心性之学只能塑造一些具备高尚道德品质的个体,却难以落实到疆域广袤的政治体之中。 这一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荀子补足的。荀子目睹战国中后期大规模政治集团兴起,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修正了不少之前儒家政治思想的内容。荀子也强调礼制,但他从凝聚“群”的角度出发,将礼制从较小共同体的行为准则,扩大为支撑一个等级分明、分工明确的庞大政治体的制度根基,使“礼”兼具了“法”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并以礼为基础,通过强调后天的“学”(而非单纯的心性修养)的重要性与士人的主体意识,树立起了大一统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清人汪中认为,儒家经典多由荀子后学保存、传播,从主导意识形态的建立与普及的角度而言,这一观点很有道理。近人李源澄尝言:“荀卿明王道、述礼乐,因世所需,大畅厥辞,儒家之用,于是乎咸在,举而措诸天下不难”。[3]可以说,正是由于有荀学,儒家思想才有可能成为后世大一统王朝的主导学说。否则,即便儒家学说与中国古代的乡村基层社会如何契合,也难以有效提供大一统王朝足够的理论资源与施政纲领。 因此,所谓“儒法传统”,其理想模式或许就是以主要源自法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运作机制为基盘,以儒家的施政原则与价值理念为核心内容,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既体现儒家的民本、亲亲、长幼有序等政治理想与伦理准则;又彰显法家式的循名责实、量能受官、“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等政治原则,维持大一统政权的基本政治运作。当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流变中,这些因素能实现多少,以怎样的形式实现,是代有不同的。 02儒家的政治整合功能及其限度 关于儒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作用,陈寅恪指出:“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4]正如其言,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政治影响极大。在这其中,尤需关注儒家对于古代政权实现政治整合——即将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有效地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中,确保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政治稳定与政治认同——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首先,从汉代开始,儒学以经学为基本形态,成为了官学,构建了一套在古代社会里大体完备且能够自洽的国家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各项政治活动,并将其普及至各地,成为教育领域的核心内容,这样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正如李源澄所论:“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既为吾国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规模;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5]犹有进者,作为官学的儒学,其实高度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的内容,不断充实、深化儒学自身的体系,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局面。例如对汉代政治儒学影响极大的董仲舒,其学术“虽以儒为本,实有取于各家而成其汉代之新儒家。五行之说取之最多,意在证明儒术,非阴阳家也。于道法两家,取其权术以行其仁义,其根本精神仍为儒家。仲舒欲建立宗教政治学术合一之学说,故有取于墨家之天志学说。墨子言天志,故言兼爱,仲舒于其兼爱说亦有所取,但用之于政治,不用之于私人,此其所以异也”。[6] 其次,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这一“德”要想在幅员辽阔的政治体中实现,离不开一套完整而详细的礼仪制度,然仅凭礼治,难以充分达到约束、惩戒之效,故需以刑法律令为辅弼。对此,瞿同祖的分析极为精当:“礼是借教化及社会制裁的力量来维持的,一个人有非礼的行为,他所得的反应不外乎舆论的轻视、嘲笑、谴责或不齿,《礼记》所谓‘在执者去,以众为殃’是,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法律则借法律制裁来执行,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或有组织的制裁。但礼亦未尝不可以法律制裁来维持、来推行,而无揖其为礼。同一规范,在利用社会制裁时为礼,附有法律制裁后便成为法律。成为法律以后,既无害于礼所期望的目的,也不妨害礼的存在”。[7]以儒学为指导的政治实践,将德治、礼治与法治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在树立基本政治规范的前提下,保证政治行为与社会伦常高度契合,既能促进政治凝聚力与向心力,又能给各级为政者以无形的监督,使其在政治活动中有所惕惧。这样就在古代的经济基础之上实现了政治整合的效果。 最后,由于儒家主张“有教无类”、“选贤与能”、广兴教化,因此从汉代开始,历代王朝都较为重视人才选拔与官吏任用(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除外)。儒家经典成为有志于进入政坛之人的必要知识储备,这一方面能够不断扩大王朝的统治基础,让更多的出类拔萃之士通过进入政权来实现阶层流动,一方面又能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让更多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更多群体接受基于儒家学说的伦理规范,成为这些规范的主动践行者与维持者,形成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巩固社会秩序。特别是宋代以来,随着印刷技术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儒家典籍可以在社会上流行,统治集团主动采取重视文教的政策,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士人也大力兴建书院、社学等教学场所。而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门阀贵族势力在五代十国纷乱之局中消亡殆尽,使社会流动成为可能。今人所谓的作为宋代官僚政治根基的“出身寒微的非身份性地主和官僚,不享有士族的种种封建特权,不能够世官世禄”的“庶族地主”群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出现的。[8]而明清时期盛行于基层社会的乡约、善书,使民间的礼教秩序与王朝的政治秩序有机衔接起来,由服膺儒学的士绅作为地方精英维持秩序,从政治整合的角度来看,大大节约了治理成本。 当然,必须看到,儒家的政治整合功能也有其内在弊病,当这些弊病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难以制定克服之道,便是统治秩序遭遇危机之时。儒家讲求礼治,而礼治的核心就是等差有序,强调政治等级与社会等级存在的必要性。这固然有助于在古代社会条件下维持基本秩序,但如果基于这些依礼制而形成的等级导致分化严重的经济差别,其结果,一部分位于较高等级的群体攫取大量社会财富,位于较低等级的群体连实现温饱都困难时,就会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引起民变。加之儒家学说里固然有维系基本秩序的一面,同时也有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从直指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均贫富”、“正经界”,到承认政权更替之合理性的“汤武革命”论与“异姓改代,天命扉常”说,每当社会危机到来之时,这些指向鲜明的思想就弥漫于社会。例如明代的皇室与勋贵霸占大量土地,驱使自耕农成为其佃户,并且兴贩牟利、怙势豪夺,垄断了大量社会财富。[9]最终激化社会矛盾,是促成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从汉代开始,以儒学为主导的政治秩序,离不开士绅阶层的辅助。毛泽东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10]士绅阶层在古代社会里固然有其重要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功能,但这一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垄断文化资源、掌握经济资源。从汉代的累世经学之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再到明末权势极大的地方乡绅,虽然其支配形式与经济基础各有差异,但其权势常常足以武断乡曲、兼并土地,使政府的编户人数减少,同时垄断政治资源,扰乱政治秩序,最终造成政治动荡。 03法家传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虽然秦亡之后,法家学说屡受历代儒者批评,但作为一种政治传统,其在中国历史流变中依然具有影响。正如萧公权所言,从中国古代政治的整体面貌来看,“古人所谓‘法’是指整个的政治制度。其精神与‘礼’有异,而其范围则与礼相同。孔子政治哲学包含了一个正名的原则,荀子传之而为礼治,韩非李斯再传而变为法治。古代亲亲的宗法社会既转变而为战国以后贵贵的政治社会,礼治当然会随之转变而为法治。假使秦汉以来二千余年之中没有法家所立的学术及制度,虽有孔孟的道德仁义,恐怕是‘徒善不足以为政’。中国人民虽未必弄到‘披发左衽’的地步,中国社会必然难免江翻鼎沸的危险。照这样看来,法家之功真不在禹下”。[11]例如汉代虽奉儒学为官学,但律令之学依旧流行。不少儒者兼习经学和律令,用治经之法治律令,汉廷选拔官吏,也以是否明律令为重要标准,因此各地私家传授律令之风甚为普遍。[12] 《商君书·赏刑》曰:“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韩非子·有度》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相比于重视礼治的儒家要么强调要“原心定罪”,要么主张根据不同身份等级制度不同的惩处标准,法家的治理风格体现出古代社会里的难得的平等精神。这正如吕思勉所论:“法家之义,则全绝感情,一准诸法。法之所在,丝毫不容出入。看似不能曲当,实则合全局,通前后观之,必能大剂于平也”。[13] 此外,吕思勉又言:“凡为国家社会之害者,非把持则侥幸之徒。把持谓已得地位之人,侥幸则未得地位,而思篡取之人也。法术家务申国家社会之公利,故于此曹,最为深恶痛绝”。[14]法家的这种施政风格,在古代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公平,保障平民利益。章太炎认为,从中国古代职官变迁来看,上古治民之官,独有士师,随后士师权分为二,长民者谓之吏,治事者谓之司,法吏之职,由是焉出。因其擅长书契文史,故听讼决狱,亦有兼顾,公牍往来,润色文字,尤非法吏莫能为,久而久之,其地位在整个职官体系中愈显重要。后世法吏,临民理政,“必身历其壤,手写其图,持筹以计之,著籍以定之,上之长官,以知地域广轮、户口多少之数”。[15]此一强调综核名实、行事判狱一准于法的特点,影响着后有心为民请命官员。因此,“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国家者,不在经国远猷,为民兴利,特欲综核名实,略得其平耳。是故韩、范、三杨为世名臣,民无德而称焉。而宋之包拯、明之况钟、近代之施闰章,稍能慎守法律,为民理冤,则传之歌谣,著之戏剧,名声吟口,愈于日月,虽妇孺皆知敬礼者,岂非人心所尚,历五千岁而不变耶?”[16]从历代致力于打击豪强、摧抑权贵、保全民众利益的官吏身上,可以看到颇为明显的法家风格。而也正由于有着这样的政治传统,才能较为有效地消除因儒家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政治弊病。 相似的,每当历代王朝出现较为明显的利益集团,进而导致政治风气败坏、政治效率低下、中央权威丧失、法令形同具文、经济与社会资源屡遭中饱之徒侵吞等现象时,时人多从法学传统中寻求挽救改良之道。如东汉中期以后,世家大族屡屡干预朝权,地方上的豪强兼并土地、欺凌百姓,铨选制度漏洞百出,请托结党之风盛行,政治危机愈发明显。崔寔目睹斯景,认为:“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政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17]主张统治者师法汉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18]尽管东汉政权由于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早已病入膏肓,因而未能实现崔寔、王符等人倡导的依据法家之道振衰起微,但曹操在北方明赏罚、立纲纪、兴屯田,诸葛亮在蜀地打击当地豪强,建立政治秩序,都是在运用法家的政治传统。可以说,从东汉末期,到三国鼎立,是一个法家大行其道的时期。曹操与诸葛亮虽然并未统一全国,但至少在较大的范围内实现了政治与社会稳定,为恢复经济生产创造条件。 犹有进者,章太炎指出:“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19]要想践行法家之道,就要求为政者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精湛的政治能力、高尚的政治道德,能够驾驭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能够应对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集团。因此,法家传统虽然强调法令典章的重要性,但其实对为政者本身的要求是极高的。这在逻辑上反而与儒家强调的“以不忍仁之心,行不忍仁之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颇为相似。比如晚明重臣张居正力行改革,颇具法家之风。他对友人言:“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20]他主理朝政之后,自言:“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且受恩深重,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21]其风尚之高,于此可见。 但也正因为这样,其实在中国历史流变中也就很难出现真正秉持公心力行法家之道者。法家主张“治吏不治民”,而一旦要触及政治体系中的中饱群体,必然会导致一系列政治斗争,这不但需要审时度势,雷厉风行,而且还需不计毁誉,以天下苍生为念,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总之,其对理想为政者的标准不亚于儒家所向往的圣君贤相。但在政治活动中,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人其实寥寥无几。而如果不具备这些品质,法家所论述的“法”、“术”、“势”很可能就沦为假公济私、以权行恶的工具。汉代的张汤、杜周之所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最后,“凡法家,以为人性忮駻,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22]法家对人性的认识颇为悲观,因此着眼于设置各种制度与法令,运用赏刑二柄,保证政治秩序之稳定。这样一来,必然会使政治权力覆盖于社会。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地方上有各种宗族与乡里组织,虽然可以通过任命官吏或倚靠地方精英来治理,但政治权力与乡里秩序之间依然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强行将前者纳入后者,难免不引起矛盾冲突。更有甚者,法家式的政治对行政效率与动员组织能力要求极高,在短时间内秉此治国,或许能收循名责实、整军经武之效,但行之日久,则会导致过度消耗社会资源,致使民众疲惫不堪。对此,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之《原道篇》里指出:“政之所行与俗之所贵,道固相乏,所赏者当在彼,所贵者当在此。”[23]法家强调综核名实,容易流于于严刑峻法,在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忽视民众由长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生活习俗与心理诉求,而后两者正是在政治活动之外大多数人不断在日常活动里践行的行为准则。这样,“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所以法家政治传统的最主要缺点就是“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24]秦之所以速亡,历代行法家之政者难以持久,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04余论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些海外学者与港台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没有政治实体意涵的“文化”,而是有着一套延续两千余年的政治与社会治理体系,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具体实践中,这一体系在应对各种时代危机之时,不断完善自身,丰富其政治内涵,是一项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此乃今日认识儒法传统的基本前提。而儒法传统各有特点,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维系着广土众民的政权,实现基本的政治与社会稳定。要想较为全面的认识中国传统政治,儒法二家各自的影响皆应重视,不可偏废。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它们各自存在的一些症结。 如果将眼光转移到近代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主要是西欧)传统的封建体制开始瓦解,各个政治实体之间战争不断,统一的民族国家应运而生。这使得中央政府具有极大的权力,过去各种割据的、分裂的地方特权渐渐被中央权力所整合。其次,新出现的民族国家具有极强的政治与经济汲取能力,主要表现在动员领土内的大量民众成为战斗兵员,以及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税收能力。而新兴民族国家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诉诸于民族主义的宣传,宣扬所有国民皆属于同一民族,具有平等的政治身份,以此来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以及形成比较有效的政治动员与政治整合能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在如何有效动员与组织广大人民成为时代的主要课题之际,能否根据实践而提出一套自洽的治国之道,将儒家的民胞物与和法家的循名责实容纳其中,保证执政集团的道德品质与理想信念,克服官僚组织的各种痼疾,实为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人必须直面的大问题。
注释 [1]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载《吕思勉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19页。 [2]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3] 李源澄:《诸子概论》,载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李源澄集新编》第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51页。 [5] 李源澄:《经学通论》,载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李源澄集新编》第1册,第6页。 [6] 李源澄:《秦汉史》,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265页。 [7]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48页。 [8]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载《朱瑞熙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9] 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明代勋贵兴贩牟利怙势豪夺》,载《王毓铨史论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5—609页。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页。 [11] 萧公权:《诸子配孔议》,载《迹园文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12] 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载《秦汉史论稿》,台北:三民书局2019年版,第235—295页。 [13]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载《吕思勉全集》第3卷,第418页。 [14]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载《吕思勉全集》第3卷,第419页。 [15] 章太炎:《官制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8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 [16] 章太炎:《官制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92—93页。 [17] 孙启政校注:《政论校注 昌言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6页。 [18] 孙启政校注:《政论校注 昌言校注》,第71页。 [19]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商鞅》,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63页。 [20] 张居正:《答吴尧山言弘愿济世》,载《张太岳集》中卷,北京:中国书店2019年版,第100页。 [21] 张居正:《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载《张太岳集》中卷,第114页。 [22]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变》,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43页。 [23]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第115页。 [24]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第115页。
文章来源:雅理读书微信号2022-1-3. 原文出自《履正而行: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版。作者简介: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