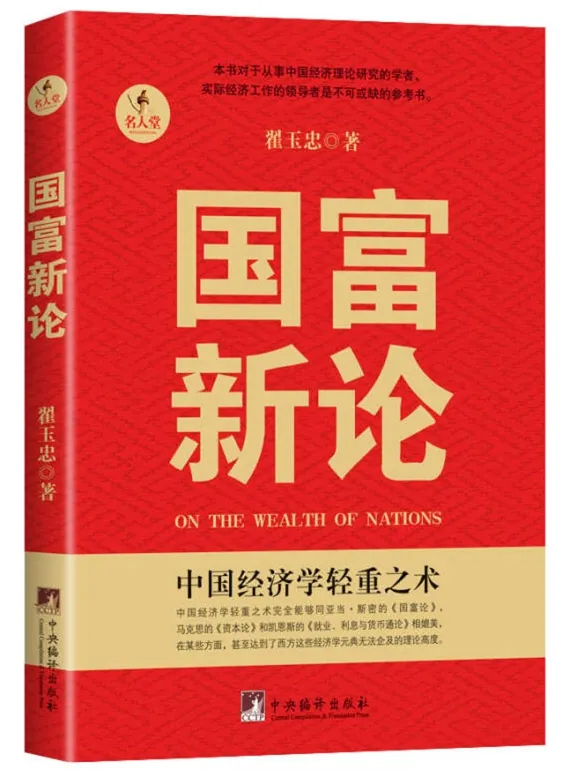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内部的平衡机制之外,还有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平衡机制。这在周礼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第五十二》甚至将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孝道联系了起来,主张砍伐草木要有定时,猎杀禽兽要有定时,并引孔子的话说:“砍伐一棵树,猎杀一个禽兽,不在合适的时候就不是孝。”(原文: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亲亲至于爱物,由爱物亦及亲亲,所以说不按时取物是不孝——中国文化其博大如此! 按照《礼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即对生物的保护,对森林的保护和对矿产的保护。比如狩猎的礼,其核心就是对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礼记·王制第五》谈到田猎时应遵循的法则时说:没有祭礼、战争却不打猎就是不敬;打猎不依礼仪,随意捕杀就是作践天地所生之物。天子打猎不可一网打尽,诸侯打猎不可成群捕杀。天子射杀野兽之后,要放下指挥用的大旗,诸侯要放下小旗。天子诸侯停止捕杀而大夫接着打猎,捕杀之后就下今协助捕猎的佐车停止,佐车停止后,百姓才可以打猎。正月之后,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的官吏在沼泽河流中放入拦水捕鱼的工具;九月之后,可以张设罗网捕鸟;九月草木凋零飘落之后,可以田猎;八月之后,可以进入山林,昆虫还未蛰伏在草里,不可以焚草肥田,在打猎时,不可捕杀幼兽,不攫取鸟卵,不杀怀胎的母兽,不杀刚出生的鸟兽,不斩尽杀绝。(原文: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可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礼记·王制第五》中还将对自然的保护措施延伸到了消费环节,这一点特别值得现代人学习。因为只有在消费市场取缔某些商品,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应的自然资源。上面规定:不成熟的果实谷物,不按时砍伐的树木和不按时捕杀的动物严禁进入流通市场。(原文: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西汉贾谊在其《新书·卷第六·礼》中指出保护自然也是为丰富人类自己的物质生活,其中所涉及的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措施与《礼记·王制》所载相类。文中说:狩猎时不四面包围,不掩杀成群野兽,不射杀栖息在巢穴中的禽兽,捕鱼不把沼泽中水放干,豺不祭过兽,不去捕杀它;獭不祭过鱼,不要去网罗它;鹰隼没长成,只观看而不张网捕杀;草木之叶不零落,就不去砍伐;昆虫不蛰伏休眠,就不用火烧荒;不射杀幼鹿,不取卵,不剖腹取食未出生小动物,不在兽未长大时捕杀它;鱼类未长大不捕捞作祭品,秋天鸟兽未长出毫毛,不猎取食用。捕获它们按节令,使用财物要有节度,那么生物就会繁衍增加。(原文: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眭而不逮,不出颖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育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 贾谊在文中所说的“用之有节”,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通过基本商品的储备(农业时代主要指粮食),有效地抹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市场波动。难怪他称礼为“养民之道”。《新书·卷第六·礼》中说:国家若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若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紧急;若没有三年的储备,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百姓耕种三年一定能剩吃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一定能剩够三年吃的粮食;这样连续三十年,就有了十年的积蓄。即使有大旱和水涝之灾,百姓也不会挨饿。然后天子才可以备置佳肴美味来享用,每天都饮宴奏乐。诸侯按时享用美味佳肴,敲击所悬之钟鼓使之高兴……所以礼是君主自我遵守的规章,蓄养百姓的措施。(原文: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民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相通,而有十年之积。虽有凶旱水溢,民无饥馑。然后天子备味而食,日举以乐。诸侯食珍不失,钟鼓之县可使乐也……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 《礼记·王制》中也有近乎相同的论述,所不同的是,《礼记·王制》的作者特别规定冢宰以三十年的平均收入来编制年度的预算,“量入以为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反对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和纵欲的消费主义,这是至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观点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文中说:冢宰编制下一年度国家经费的预算,必定在年终进行。因为要等五谷入库之后才能编制预算。编制预算,要考虑国土的大小,年成的丰歉,用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数作为依据来编制预算,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如何开支。祭祀的费用,占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遇到父母之丧,虽然在服丧期间的三年内不祭宗庙,但天地社稷之神却照祭不误,因为天地社稷之神比父母还要尊贵。丧事的开支,用三年收入的平均数的十分之一。丧事和祭祀的开支,超过了预算叫做“暴”,决算有余叫做“浩”。(原文: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 综上所述,对内社会不同阶层的平衡,对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才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基因,而这些思想皆可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礼制。今天,古老的周礼早已经分化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中国,这个五千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发源于东亚大陆上的生态文明,至今仍奔流不息;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超越以无限欲望掠夺有限自然资源为基本生存方式的西方现代文明,将人类带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