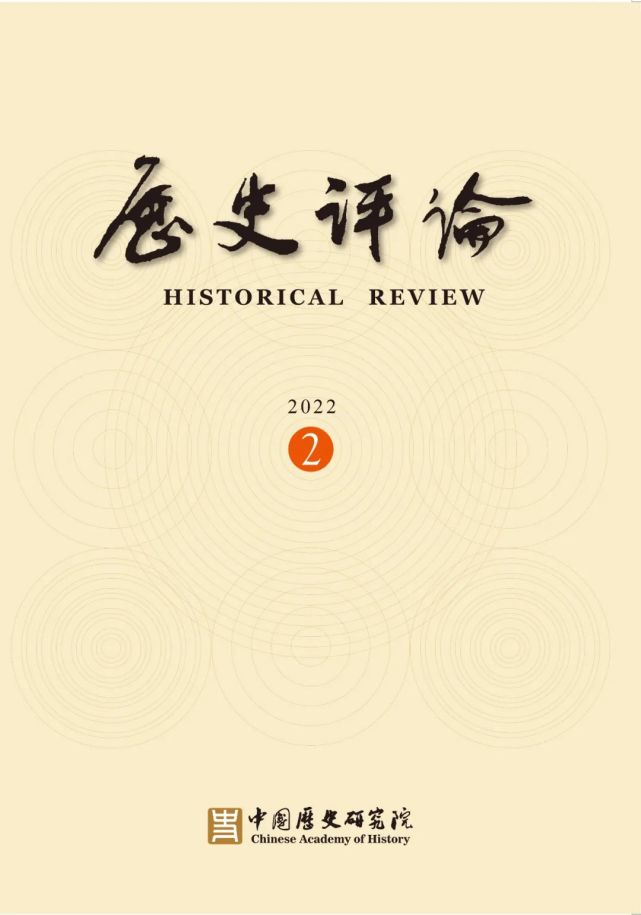从“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到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与主体任务,中国古代法律以其强制力予以维护。在中国古代,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强制性手段,有效支撑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各项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
文明及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必须实现对政府、社会、个体的规范化制约。中国古代法律从国家治理核心目标、权力配置运行、民间私权关系等方面,加强对国家与社会的规制,并通过长期发展,探索、铺就了一条极富特色的东方大国法律治理之路。
以维护中央集权为核心目标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人众地广的文明大国,在漫长发展过程中,独立探索,自我完善,形成了特色鲜明、成效卓著的东方大国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的核心内涵有二:“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古代法律从制度、思想到文化,都将维系“大一统”国家格局、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列为首要目标。
中国古代法律主张“仁政”、“德治”、“轻刑慎罚”,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迁就。根据法律,地方势力或个人的叛乱、割据、分裂行为,属于严重犯罪。对此,历朝法律均规定处以严厉刑罚。汉律规定,据城池要塞叛乱或向叛乱者投降等行为,均构成严重犯罪而处以极刑。南北朝时期,《北齐律》将“叛”、“降”等重大犯罪列为“重罪十条”。隋唐至明清,法律均设谋叛罪,并将其列入“十恶”,给予严刑惩罚。
维护“大一统”国家格局需要保持全国政令统一,由此中央政府才能有效调动全国各类资源以实现国家意志。大量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古代中国唯一有效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在于:制度与法律全国统一,重大事项由朝廷决定,公权资源统一调配。
首先,国家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统一行使。中国古代在国家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形式方面,遵循“分事不分权”原则,具体管理事项和管理职责,可以由不同机构分别行使,但核心权力不得分割。最高决策权、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执行权,均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统一行使。
其次,法律明确规定并严格控制地方权限。在明清两代法律中即严格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中央权限,在法律中通常称“钦部权限”, 包括皇帝权限与朝廷部院权限。地方各级官员的管理行为若涉及“钦部权限”,必须履行奏请、咨申程序,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对应咨申部院而不咨申、擅自行动者,主官要受行政处分;对应奏请皇帝而不奏请者,主官行为构成犯罪,要受到刑事处罚。
最后,强化中央监察,确保中央政令与国家法律在全国各地得到遵守与执行。中国古代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并制定了严格的监察法规。汉武帝时,针对一些地方官吏不听朝廷政令、不执行国家法律的现象,专门任命刺史,对地方官实施严格监察。刺史以“六条诏书”察按郡县,其中就包括地方官不执行皇帝诏令、不遵守朝廷政令、不实施国家法律等行为。汉以后,历代王朝先后设立御史台、都察院等机构专司监察。对各类各级官员的监察,既注重其是否贪贿营私、怠玩懈政,更注重是否忠于朝廷,是否执行中央政令,是否遵守国家法律。
规制国家权力运行
国家治理,首先必须确定涉及公权力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机制。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相沿完善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架构,并制定相应法律,既明确这一权力架构的权威性、有效性,也确定相应的运行机制,以保证国家权力合理规范运行。
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中央机构的职能不断趋于合理,规范其运行的法律也更为完善。唐代法律规定,三省各有职掌,在职掌范围之内,各自独立、依法行使职权;但对重大国务事项,由门下、中书二省长官会商共议,提出处理意见。官员可就政事发表意见,上表朝廷。为防止所上表文被某一机构扣压,保证所提建议顺利上达,由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侍御史三人,共同收受上表。法律规定,重大刑事案件由中书、门下长官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通过三部门共同参与,既协同配合,又相互制约,以求案件审理合法、公正。
明清两代全面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为确保皇权与中央集权的稳定实施,法律明确设定国家权力布局,并规制权力机构的运行机制。清朝统治者尤其注重通过颁布实施“会典”这一法律形式,以规定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在统治者看来,“会典”乃“国家立纲陈纪,布在方策,所以明昭代之章程,备诸司之职掌,以熙庶绩,以示训行,典至巨也”。如嘉庆朝《大清会典》规定,军机处“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理机务”;内阁“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对国务执行机构中的吏、户、礼、兵、刑、工等部院,也分别明确规定其职掌、权限及责任。
清代法律还对国家权力机构的运行机制进行规制。皇权代表国家最高权力,代表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皇权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决策权上。为保障皇帝决策权不受其他因素干扰侵夺,也为保证皇帝决策权稳定、规范地行使,法律从决策方式、决策程序、决策依据等 方面,设置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决策机制。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决策方式主要分为本章批答、御门听政两种。在本章批答方面,凡属皇帝决策范围之事项,无论直省督抚,还是部院堂官,都必须进呈本章,请示皇帝。皇帝则通过批答本章,颁布谕旨,履行决策职责。法律还在进呈资格、通政使司形式审查、部院议奏、内阁票拟等环节,详细规定了本章批答中的前置程序。
九卿会议是清代朝廷重要议事机制之一。涉及国家重大事项,皇帝可启动九卿会议议事程序。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参加的九卿会议,可“详议国是,均平政刑”。针对所议事项,如果九卿成员意见不一致,必须各具意见,上奏皇帝。针对九卿参与国务讨论活动、履行决策辅助职责,法律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纪律要求,对无故不按时参加九卿会议者要给予处分。
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着重点
中国古代对民间经济活动,采取总体管控、谨慎制约的原则。对于以财产关系、经济交往为主的民间私权关系,主要通过国家法律、礼治规范、民间习俗等途径进行调整。其中,国家制定法主要针对不动产所有权、买卖借贷、合同契约、债务清偿中的重要原则进行规制。

田宅买卖既涉及国家财政收入及社会秩序稳定,也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如清代法律明确规定,从直省布政使司,到州县正印官,在民间田宅等不动产买卖中,分别履行不同职责,“凡民间卖买田宅,皆凭书契纳税于官,以成其质剂,曰契税。税契之法,布政使司作契帖,钤以司印,颁之州县。民之卖买田宅者,领契帖于官,征其税,书其姓名,揭其物数,并原契予之,以防诈伪,以治诉讼”。这里既强调田宅买卖必须“纳税于官”,又注重通过官府对民间买卖行为进行确认,以防止围绕田宅的欺诈行为,并为日后涉讼之时,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上的有效保护。
借贷作为一种与财产关系相关联的民事行为,在解决民众急需、活跃市场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借贷行为也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因此,对借贷行为进行规制十分必要。如唐令即规定民间借贷行为中的最高利息标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并规定借贷时间不论多长,利息不得超过本金。清代法律也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制。《大清律例》设“违禁取利”罪名,对违反借贷方面有关禁令者给予惩罚。为防止主管官吏利用职务之便放债牟利,《大清律例》特别对放债主体作了限制,其中规定官员不得于所辖范围内为收取利息而出借钱款,即便按照社会通行的普通利率标准放债,也构成犯罪。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宗法关系。清代法律对与宗祧继承相关联的重要事项,进行明确规制。《户部则例》“户口门”下设“继嗣”条,从四个方面对宗祧继承作了详细规定;《大清律例》设立“立嫡子违法”罪,对宗祧继承方面种种违规行为给予处罚。在家庭关系中,财产继承是最易产生纠纷并进而对亲属关系、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领域。历代统治者都注重以法律手段规范财产继承关系,如唐代法律规定,财产继承以“兄弟均分”为原则,并对财产继承方面的特殊情况,分别作出详细规定。
实现国家和社会管理有法可依
华夏文明绵延至今,始终在整体上保持统一、稳定、发展、进步的方向。中华文化宽广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华夏文明5000 余年绵延不断的遗传密码与文化基因。这其中,富有特色而行之有效的中国古代法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到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与主体任务,中国古代法律以其强制力予以维护。在中国古代,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强制性手段,有效支撑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各项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到了清代,国家通过立法,为职司中央政务管理工作的30 余个部院,分别量身定制了专门法律,以规制其职掌权限、责任义务、办事程序、议处议叙等;对部院中某些职能重要的内设之司,亦制定专项法律。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各级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国古代法律中,以规制公权力配置与运行为主要任务的“公法”较为发达。唐、宋、明、清各朝,针对国家权力结构、公权资源分配及各级权力运行机制,乃至文武百官管理,形成了系统、详备的法律体系,既保障了权力配置的合理性,也提升了权力运行的有效性,进而在整体上使得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合法、有序。
在私权领域,古代法律以特殊方式给予关注。无论对与国家宏观政策直接相关的不动产买卖、市场管理、契约纠纷,还是对属于“民间细事”的宗祧继承、财产继承、私人借贷等民事关系,一方面,以国家制定法和地方性法规进行法律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地方官确认的方式,将民间习惯、宗族规训乃至“礼”的规范,纳入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依据之中,并基本实现法律规范对民事关系的全覆盖。
中国古代法律萌芽、产生并成长于中华文明的制度环境与文化土壤之中,为社会秩序构建、国家长治久安作出了重大贡献。全面总结中国古代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功能作用,有助于丰富中华文明史的内涵;同时,根据“时为大”的原则,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古代法律的优秀资源,也有助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