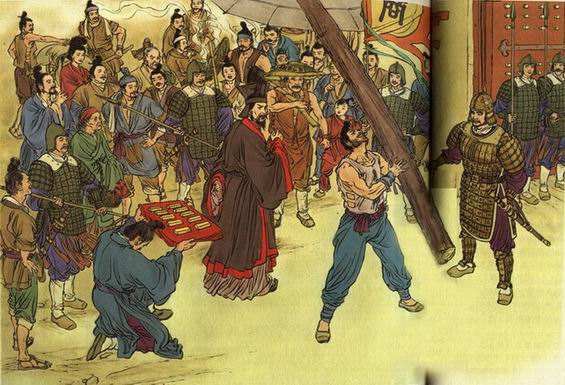最近《商君书》似乎很火爆,一批“学者”用《商君书》来否定商鞅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政治,很是有趣。不过,这批“学者”既不愿意拿出先秦典籍来考究《商君书》特别是“驭民五术”系商鞅所著,又不能拿出秦书汉简来论证商鞅施行了“驭民五术”,仅凭一部来历不明的《商君书》就能过一把“学者”的瘾,让人不得不佩服江山代有“才人”出。 《商君书》长期都被怀疑是“伪书”,至少有大量篇幅系后人伪作。《韩非子·内储说上》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的《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这说明《商君书》应该包括《开塞》、《农战》等篇。《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殆法家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一些“学者”不加考究,单凭《商君书》来“做学问”,这已经不是“治学”而是“伪学”,还自以为做学问多容易,悲夫。 司马迁虽然痛恨商君刻薄寡恩,但也承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后来刘邦在彭城惨败,就是依靠萧何从秦地运来的援兵与粮秣坚持战斗,商鞅变法客观上为“汉并天下”提供了物质条件。商鞅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实干的政治家,从“诸侯卑秦”到“诸侯西来”,其贡献不是一句“掠夺”可以解释。韩信说项羽不该不居关中而居彭城,张良支持刘敬定都关中的意见,都认为关中沃野千里经济富庶,而关中经济繁荣的根基就在商鞅变法。 荀子入秦,在《荀子·强国》篇中认为“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虽然认为秦国“无儒”存在不足,不应该只靠强力,但也承认秦地民风纯正,无论是百姓、官吏还是士大夫、朝廷都值得肯定。六国人才如水之归海,纷纷前往秦地,也说明秦国政治清明更能选贤任能。 一批“伪学者”甚至认为《商君书》是古代太傅教太子的“绝密文件”、“天下第一禁书”,却不知如何这些“学者”如何考据、如何解释为何编入《四库全书》。治学需要从证据出发,研究历史更应该考虑当时历史典籍,岂能信口开河?当年就有学者否定武则天杀死自己女儿栽赃王皇后,理由是如果真如此为何唐高宗废掉王皇后的诏书不记载此事,骆宾王痛骂武则天也不涉及此事?这种“你知我知”的“宫廷秘闻”又如何传扬出来?司马光对“存疑”的史料往往不置月份,《资治通鉴》对此事记载就是至于篇末没有具体时间。这种态度才是“治学”态度,“大胆假设”后需要“小心求证,这才能得出重要结论。 把中国遭受第三次蛮族入侵带来的近三百年落后当成中国几千年都落后,把中国现在的落后规则为两千多年前的秦皇、汉武甚至孔子、商君,这些“伪学者”究竟是如何展示他的逻辑?不敢批评时弊,就批判古人,难道他们的“勇敢”只能是对前人“鞭尸”而不是“面刺”或“谤讥”?批判商君“驭民五术”,总需要拿出史料特别是秦书汉简论证商鞅“怎么做”吧?言之凿凿说即使《商君书》不是商鞅所作,也是商鞅行为与观点的综合,治学者总要拿出典籍资料“举证”论证商鞅做了哪些《商君书》所列措施吧? 此外,用今日都不能实现的社会理念去苛求古人,痛骂他们这些“失去抵抗能力”的历史人物当然很容易,“打死老虎”很有趣否?商鞅是政治家,西入秦出色完成了秦孝公交给的改革任务,影响秦国发展一个半世纪,这当然需要肯定。至于秦朝二世而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秦二世背法去势,施行暴政。而且秦始皇大量接受韩非子“法势术”融为一体而不是商鞅那样“重法”,岂能把板子打在商鞅屁股上?各位学者出出主意,在当时商鞅如何才能短期内让秦国发展起来避免“诸侯卑秦”?难道是为了“百无一用”的书生小骂两句宁可被魏国蚕食?难道依旧是“干多错多”、“不干有理”? 一梭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