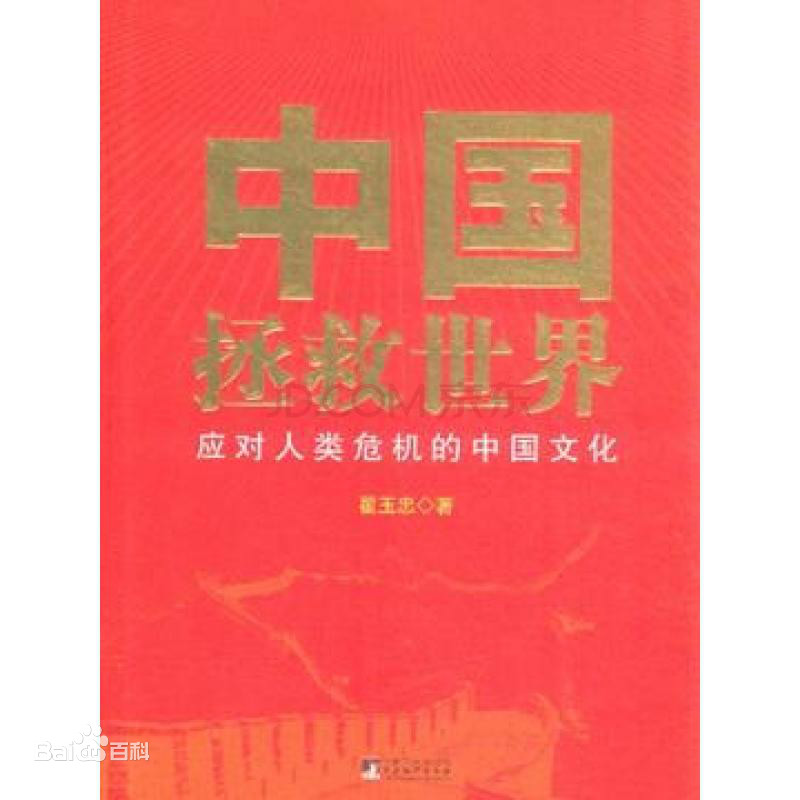隋唐时期,儒家受到佛道两家的冲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李唐王朝重佛、宗道的政策加剧了儒学衰微——特别是在唐高宗李治于公元649年即位以后。《旧唐书·儒学传》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浓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知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 连国子祭酒(太学校长)这一重要职位都不再由儒学大师担任,可见当时儒学的境地。安史之乱后,宦官鱼朝恩兼判国子监,这位不学无术的家伙竟登上讲台为百官讲解儒经。唐高宗时身为礼部尚书的许敬宗为支持武则天当皇后,要废掉王皇后,他给出的理由竟然是:农夫多收了十斗粮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乎!在唐代,儒学常常成为廉价的政治遮羞布。 在儒学式微的情势下,对儒学本身的反思也在进行,宋明理学家们用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等方法重树立起新儒学大旗。不幸的是,宋明理学对心性的重视并没有使自己回到道家“内静外敬”的基础礼仪规范,反而从佛教那里不恰当地承袭了“灭人欲”的禁欲理论。 古圣先贤长期以来反对人被外物同化,物欲横流,认为这样做会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上文所引《礼乐·乐记》中就有:“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反对“灭天理而穷人欲”并不是赞同“存天理而灭人欲”,它只是在强调“因人情,节人欲”——从“因人情,节人欲”到“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中华礼义文明落入黑暗时代的重要标志。 可能很早就有人主张灭人欲,因为《荀子》对灭欲和寡欲的思想进行过激烈地批判。他说凡是谈论治国之道而依靠去掉人们的欲望的,是没有办法来引导人们的欲望而被已有欲望难住的人。凡是谈论治国之道而依靠减少人们的欲望的,是没有办法来节制人们的欲望而被人们过多的欲望难住的人。《荀子·正名第二十二》云:“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 荀子认为性情是人类的本性,不可能去除,但却可以节制,所谓“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第二十二》论证说: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大意是:本性是天然造就的;情感是本性的实际内容;欲望是情感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想要东西而去追求它,这是情感必不能免的现象;认为可行而去实行它,这是智慧必定会作出的打算。所以即使是卑贱的看门人,欲望也不可能去掉,因为这是本性本具的。即使是高贵的天子,欲望也不可能全部满足。欲望虽然不可能全部满足,却可以接近于全部满足;欲望虽然不可能去掉,但对满足欲望的追求却可以节制……正道是这样的:进则可以接近于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退则可以节制自己的追求,天下没有什么能及得上它。) 程朱理学违反人性,一直受到海内外广泛地批判。“贬日崇华”的日本大儒荻生徂徕(1666~1728年)曾批判说:“人欲者,人之所必有而不可去者也。程、朱乃言‘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岂不妄哉!”实际上理学的“灭人欲”是扭曲,而不是“存”了天理或自然之道,因为人欲是自然的一部分。 台湾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曾经以作家特有的笔触为我们这样描画宋明理学家的本来面目:“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这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第七任皇帝赵煦登极那年(一○八五),只有十岁,正是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课时,偶尔折了一枝柳条来玩,程颐立刻正色阻止说:‘春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赵煦把那枝柳条悻悻扔掉,气得发抖。对一个十岁顽童,就作如此压制,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斫丧人性。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柏杨将十二、三世纪宋明理学兴起后称为中华文明的“大黑暗时代”。当诸子百家都成了异端,当无数的贞节牌坊在中华大地上树起的时候,曾经以复兴礼乐为己任的儒家最后窒息了中华礼义文明。 直到今天,国人还没有能够恢复中华礼仪文明昔日的光荣,世人还不知什么是内静外敬,“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道。曾几何时,有人无知地将孔子的“克已复礼”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同起来。孔子肯定人性自然,事实上他所谓的“克已复礼”与现代的克已奉公具有相近的社会含义,尽管二者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