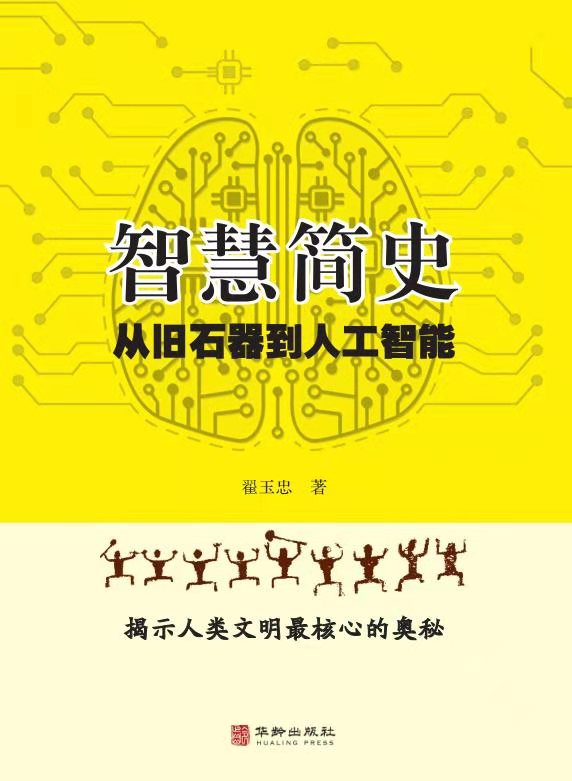北京知名学者仲大军先生古道热肠,多年来乐于提携后学。最近,仲先生给我留言,谈及儒家与法家,及德法并用的治国理念。感念先辈学者教之谆谆 ,嘱之殷殷,做此文,向仲老师汇报。仲老师说:“千万别把儒家与法家分开,孔子执政,相鲁,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一文一武,相辅相成。孔子杀少正卯,杀齐国优倡侏儒,是典型的法家手段,决无心慈手软。“法家是晚起的学说,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它从儒家分离出来,偏重于法的作用,像商鞅就走向了极端,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现象。一旦天下稳定下来,法的作用就减少了,儒就唱主角了。所以,用儒还是用法,用文还是用武,是根据时代而定的,并不能一味强调哪一面。中国要是打起仗来,就没法完全靠思想教育了,就要使用严刑峻法,强调纪律和法纪。 “你们做学问定不要偏于一端,盲目强调某一方的作用,必须有综合的知识和方法。在今天搞什么新儒家、新法家,都是学识偏于一隅的表现。”仲老师的确高明,因为他看到了孔子法家的一面,光这一点,就超过了太多学者。孔子于内政外交,用刑法对治巧言令色以立信,与商鞅徒木立信,无二无别。民无信不立,立信是治国的基础。读《史记·孔子世家》,就知道身处全面失序的春秋晚期,乱世用重典。孔子行政风格刚狠,势所必然。孔子三个月能使鲁国大治,不是依靠苦口婆心,诀窍是敢下猛药,以严刑峻法,得其中道。以至于齐国人担心“孔子为政必霸”!想一想,若孔子之政行于鲁国,也如商鞅之法行于秦国一样,长达六世之久,鲁国岂非东方之秦国乎?——统一天下者必非秦也,鲁也!仲大军老师引用《孔子家语·贤君》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一段,说明德法并用,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光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片面的。《孔子家语·贤君》引文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但从中只看到孔子称赞秦国“选贤与能”这一面,看不到其“法令必行”的一方面。所以前者更好。孔子认为,“秦穆公之国如此小,又地处偏远,称霸天下”的原因是:“他的国家虽然小,理想却很大。地方虽然偏僻,施政却处处合宜。他行动果断,策划事情尽量整合大家的意见。执法没有偏私,能够令行禁止。第一次提拔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就授给他大夫爵位。和他长谈三天,就把政事交给他。能这样做,可以称王,称霸还显得小呢!”(原文:其国虽小,其志大,其处虽僻,而其政中,其举也果,其谋也和,法无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羖【gǔ】),爵之大夫,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其霸少矣。)仲老师,您说法家分离自儒家,也有道理。因为法家和儒家一样,都是从西周官方学术体系王官学而来,儒家教授王官学,法家师从儒家就不奇怪了。如同我们今天上大学,都要师从教授一样。但切不可将法家看成儒家分支,从汉朝至清朝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学术分类都将法家和儒家并列为诸子之一。法家偏重于制度、法律法规,但不能说商鞅这些人就走了极端。参照孔子施政于鲁,孔子岂不更极端?您说“用儒还是用法,用文还是用武,是根据时代而定的,并不能一味强调哪一面”。个人浅见,我们不能透过西方学术特点看待诸子百家。中国学术与古希腊学术传统、学术形态迥异。中国古典学术出自王官学,而不是如古希腊哲人一样属私人学术。法家源于主司法的理官,而归本于黄老道家,儒家源于主思想教化的司徒之官,二者相互补充,相须为用,构成中华政教的主体。怎么能一会要政,一会要教呢——这不就如同我们解散司法部,只留教育部一样荒唐吗? 古人讲道德教化与政治法律的关系特别清楚,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礼乐刑政,缺一不可!换言之,一个人执政,领导社会必须用黄老法家;搞教育,必须用儒家;搞外交,就要用纵横家以及王霸术……专门研习法家、儒家,是因为专业兴趣的不同,不能说今天的新儒家、新法家是“学识偏于一隅的表现”。那研究中医之术,岂不更偏于一隅了?须知专业流派只是了解或应用中华文化的一个“工具包”,只要不存成见,终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中华文化是罕见的极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圆融有机整体。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导致其变异。举例说,先秦、汉唐,宋明儒学简直是三个儒学。我们反对儒家,是反对宋明两代佛教化、代表士绅地主阶级利益的理学,宋明理学使内圣之学玄学化,外王之学全面沉沦,国运衰弱。我们不是反对孔子、反对孟子、反对荀子……我出版的儒家类书藉包括:《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2014年);《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2014年);我还最早翻译了康有为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2009年),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也是影响极大(如果不是最大的话)的一部。另外,目前我正和石家庄学院付金才老师合作,撰写《道不可离》一书,目的是揭露程朱等理学家师心自用、援佛入儒,颠倒本末,将先秦儒学异化为宋明理学的真相。仲老师,12年前,您还曾为我的《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写序。该书目前包括韩文版和音频版在内,已经有四个版本,在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与您的大力推介分不开的。如果说,我过去20年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心得的话,就是对您这类长辈的感恩,以及对千古圣贤的敬仰。中国文化不是太古老、太朴素,而是高度复杂,高度发展,所以今人不易理解她。我通过学习经典,将所得编辑成书,总感觉是圣贤在帮助我、加持我——那一座座思想高峰是不朽的,仍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然而,目前世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仍很大,甚至诸多大学学者也不知中国古典政治学在黄老道家、法家中。我们的正式文件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而非“礼义之邦”——恐怕一些西方宗教国家和一些狩猎采集民族比我们更讲礼仪吧!中国先贤,几千年前就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持久和平的奥秘,生生大道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五千年的文化基因,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人类和平与发展,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最近出版的《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1月)一书中,我竭力阐释这一点。(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