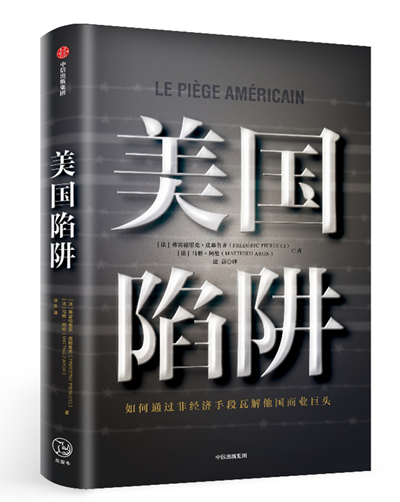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日益陷入“持久战”之际,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原锅炉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与法国著名记者马修·阿伦合作出版了《美国陷阱》一书,中信出版集团第一时间组织翻译并推出了相应的中文版。 这是一本写给法国乃至于整个欧洲人民的“警世书”,皮耶鲁齐深陷美国“法律陷阱”,切身感受美国变迁与异化,在该书“尾声”中大声疾呼:“梦醒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时机。这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法国。要么是现在,要么将永无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这是最后关头。”皮耶鲁齐在这里很有一种旧欧洲莎士比亚式的命运抉择意识: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他2019年对美国法律与司法的认知,与2013年之前对美国的某种“欧洲式信任”大相径庭。 问题的焦点在于皮耶鲁齐所称的“美国陷阱”,一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法律陷阱,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法的治权法权和域外管辖权。皮耶鲁齐具体概括了这一陷阱:“这是一场法律战争.......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中国人关注法国人揭露的“美国陷阱”,有一种特别的意味和处境相似感:其一,中兴公司案的司法过程以及“罚款+合规官”的司法和解模式,与皮耶鲁齐揭示的美国司法行为逻辑基本一致;其二,华为孟晚舟案至今悬而未决,与美国司法部对待阿尔斯通高管的“法律陷阱”如出一辙。特朗普在孟晚舟案发酵之际曾声称若中美贸易谈判需要,他可以干预此案,就是将此种“法律陷阱”予以直率的表白。只是,特朗普是个“法盲”,懂得“里子”,不懂得“面子”,口无遮拦,泄露“陷阱”机密。 当中国公司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公司之时,也就达到了美国“法律陷阱”精准打击的程度。这是中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成就,也是特定风险。因此,皮耶鲁齐揭示的“美国陷阱”就不是一种特定指向法国企业的陷阱,而是美国对全球域外公司普遍构筑起来的陷阱。中国公司和中国法律界必须从中学习如何应对美国法律风险。《美国陷阱》一书因而可以作为中国公司高管的职业培训高阶教材。 美国这一陷阱的法律构造是非常精巧的,将法律打击的每一步骤都设计和建构为有理有据的合法行为: 其一,有法可依,即美国制定了专门的《反海外腐败法》,为美国司法部的法律行动提供直接的国内法依据,但在管辖权规则上则远远超出了国内法界限,规定了长臂管辖权,其连接性因素就是美元和情报技术; 其二,选择性执法,即《反海外腐败法》在具体执法中内外有别,侧重对外调查与打击,比如根据皮耶鲁齐提供的执法数据统计,域外公司遭遇巨额罚款及不公正对待的现象非常突出; 其三,辩诉交易与极限施压,离间高管与企业/国家利益,合法实施对被告人的恐怖威吓,达成案件之外的经济或政治目标; 其四,个案司法进程与美国“秘密”保护的国内大型企业的全球化商业行动相互配合,以法律形式的合法性掩盖美国司法的实质政治化。 《反海外腐败法》是这一“陷阱”的主要法律依据。笔者相信多数人对这部法律不甚了了,尤其是美国实行判例法,要理解这一法律陷阱,不仅要看法律条文,还要熟悉数量庞大的判例案件。与美国司法部“围猎”各国企业高管相呼应的是,美国法律界的既得利益得到了极大促进,从而导致这张法律罗网越来越严密,越来越难缠,越来越成为美国利益各方共同维护、共同谋利的合作性框架。 该法建构了美国司法的域外管辖权。法律本意虽然在于禁止美国公司的海外贿赂,但由于使用了“美元”作为法律管辖连接点,使得全世界使用美元结算的所有公司都处于美国司法的管辖范围之内。 根据皮耶鲁齐的分析,这种域外管辖已广泛开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更是变本加厉。由于美元是真正“世界化”的储备货币,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由美国缔造及维系,国际贸易的结算体系由美国支配,再加上美国对互联网根服务器及全球网络情报的垄断性控制,各国企业要么保守维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低端交易模式,要么就必须进入美国国内法的管辖范围。美国对中国公司中兴、华为的指控、美国此次对伊朗石油交易的最严厉制裁,高度依赖于美国的美元霸权及全球情报控制权。 那么,美国这部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应当如何理解呢?《美国陷阱》一书尽管记述了大量事实及富有意义的法律分析,但无可避免地洋溢着一种“受害者控诉”及法国民族主义味道。这种情绪反应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美国的司法过程造成了对法律的明显滥用以及对被告人权利与尊严的不公正对待。 但是这部法律体现的全球治理中的一般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更加值得认真对待:其一,美国法观念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以国内法代替和僭越国际法的趋势,《反海外腐败法》就是显著例证; 其二,《反海外腐败法》所指向的国际贸易与商业实践中的贿赂行为尤其是“中间人贿赂”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法国企业有,美国企业也有,因而这是全球商业治理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其三,国际层面针对普遍的商业贿赂缺乏有效的国际法规制尤其是强有力的制裁机制,依赖各国自行规制又会遭遇“自己做自己案件法官”的法治困境; 其四,美国国内立法试图提供一种在国际法有效机制存在薄弱甚至空白的条件下强制规制的法律模式,是美国自我认定的全球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供给的一种替代方案,由此造成了长臂管辖权问题; 其五,美国无论具体动机如何,其长臂管辖权陷入了其他各国的“司法主权”抗争以及美国自身选择性执法的双重困境之中,既不合法,也不公正。从国际法理而言,这种长臂管辖权是一种本质上的“帝国霸权”,是未经被治理者同意的暴政和僭政。美国民主不能为长臂管辖权提供正当的政治基础,因为美国民主只能为纯粹的美国国内法律提供权威来源。 所以,这部法律的域外效力存在结构性的“民主正当性赤字”,是介乎美国国内法与真正国际法之间的“帝国管制法”。在奉行主权平等与民主法治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法律仿佛中世纪或殖民时代早期的遗迹,有待全球治理领域的制衡、批判和清理。 毕竟,美国司法部无法摆脱国内巨型企业的政治游说和压力,无法摆脱美国国家利益的限定和塑造。美国司法部是“美国”的司法部,不是“联合国”的司法部,美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是长臂管辖权的不正义性的法理要害所在。 《美国陷阱》以法国人的实证经验证伪了该法的正当性动机和基础,用大量细节披露美国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复杂过程与自身案件进程的微妙扣合关系。这起收购案惊动了法国社会,甚至引发了法国内部政治斗争,也造成皮耶鲁齐对法国政治的某种不信任。皮耶鲁齐正确看到了二战后欧美关系的不平等性,这种关系根源于美国对欧洲的“重建”及由此造成的“准殖民地化”的制度后果。 同样在本书“尾声”中,皮耶鲁齐特别提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各国逐渐默认服从美国法管辖。而直到如今,它们仍然无力设置类似的机制用以自卫或者进行反击。”实际上,欧洲对美国法的服从要早得多,从马歇尔计划及联合国体制的创制以来就已成为现实。欧洲的反击也是从零星状态到集体行动,起初是“戴高乐式”的法国反击,后来是欧盟作为整体的讨价还价,但未能形成针对美国的“去殖民化”框架。欧洲显然不是美国的“领土殖民地”,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的“制度殖民地”。美国是实质上的全球化帝国与全球立法者,好像在法律全球化层面有着丰满的理想性论述,但实质上无法摆脱国内企业集团与国家利益的“地方性”局限。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章来源:观察者网2019-5-25 编辑原文有删减
|